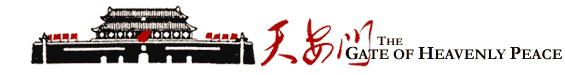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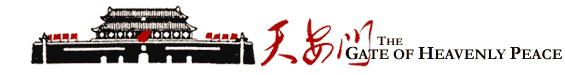 |
||||||
Forward | Note | Participants | 1 | 2 | 3 | 4 | 5 | 6 | 7 | Index
5.1 民主大学 张伯笠 5.1.1筹办 5.1.2开学典礼 5.2 撤与不撤 李禄 5.2.1撤与不撤的争论 5.2.2指挥部的情报与对策 5.2.3屠杀就要到来 5.2.4六三这一夜 |
5.3 屠城见证 李兰菊 5.4 撤离广场 封从德 5.4.1口头表决 5.4.2撤离之后 |
5.1 民主大学 张伯笠
5.1.1 筹办 〖参:李禄 4.3.3 广场后期工作 〗
成立民主大学的背景是这样,因为外地高校的不断涌入,我曾经跟外高联谈过多少次
,而且我在会上曾经讲,外地的学生应该回到本地区去。我的意思就是,你外地的高校学
生应该回到本地去搞一个天安门广场,比在这儿好。现在这样就造成有点文化大革命的那
个样子。有很多人不懂民主。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运动向更理性发展,因为当时已经决
定是不撤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已经成立。指挥部成立那天,我在联席会议的时候,跟郑
义简单商量了一下,能不能把它搞的高一点,搞什么形式。我当时提出一个比民主沙龙要
大,那么就是要办一个天安门大学。郑义表示支持,他说,“这个想法非常好,但要具体
设想怎么干?”这个框架就当时产生了,两天以后我见到了潘义,李禄就跟我说,“潘义
,这是张伯笠。张伯笠有一个设想,要办一个大学。他们也有这个想法,你们能不能合着
办?”当时我想从资金方面,包括从教员方面香港会提供很大的帮助,于是我就非常赞成
和他们合办。后来就是什么“北京的学生和香港的某大学”,中央威胁就是这样威胁的。
但是后来因为香港这个大学不同意加入人员,说可以提供资金,但是不加入人员,可以帮
助你们。
当时设计有一个联络图,把这个民主大学放在民主女神下面,就是中心。李禄也讲了
,如果民主大学办成以后,整个的组织,包括指挥部就都设在民主大学那里,把运动往一
个理性的方面发展,本身是个象征嘛。初期准备工作我就招收人员,广播里喊了多少次,
大概有六十多人报名,经过严格审查收了四十名,因为有的没学生证。要求必须是学生和
知识分子才能作工作人员,而且固定,你不能再走,不能象广场指挥部那样,今天来了,
明天就走了,这个不行,要作长期打算。在二十六日中共的电台就警告了,“现在广场有
一些人和香港某大学在搞一个什么民主大学。这个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是非法
的,组织者要完全承担法律责任。”对这个警告我们同学有的就害怕了,四十个人就退出
了八个。我就开会跟他们讲,责任由我负,他警告的是组织者,而你们是工作人员,不是
组织者,大家不要害怕,我就跟他们说,毛主席说了,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他经过那个
教委批准了?他们是培养军事人才,我们是培养民主人才。我们既不发毕业证,又不收学
费,只要来天安门广场的就是学生,天安门广场就是我们的课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就
是我们的校园,要你什么批准?我这样一讲,大家的精神就又振奋了,振奋以后就办。基
本什么都办成了,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联系教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是五月二十八日了,我就向柴玲提出辞职,一个是我要提很多资料,要保护
一个作家去写书,同时也跟封从德要一笔经费。我回到北大见到了三个教授,其中有一个
是严家其,有一个是陈鼓应。当时定的是陈鼓应讲第一课,严家其呢,我跟他说,你能不
能当我们的名誉校长,因为当时方励之是“怀抱琵笆半掩面,千唤万唤不出来”,刘宾雁
在美国爱莫能助,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觉得知识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严家其。我跟严
家其第一次谈的时候是在他的家,第二次谈是在广场,就是刘晓波绝食的时候,当时严家
其问我,“你这个民主大学宗旨是什么?”其实我们当时还没讨论这个问题,但突然就冒
出了八个字,可以用这八个字作办学方针和宗旨,就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严家其
说,“这八个字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改一个字,法制的制要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
区别很大。”我说,“这很好,我可能想的时候是那个制。”所以把宗旨也就定了。定了
以后他说,“好,我接受你的聘请,我作名誉校长。”我说“好,我们现在就筹备开幕式
。”我们定的是五月三十日开幕式,就是开学典礼。
当时撤和不撤的问题争论非常大。后来我听到一个消息,柴玲、封从德、李禄跟我讲
,说三十日要撤退。我一想三十日要撤退,那三十日成立民主大学就不可能了。我就想把
它拿到北京大学去成立,我跟我们班的同学商量,我说大家都要当工作人员,我们就把它
办在北大。只要我们这样办民主大学,北大学生就起来了,我们又掀起一个大高潮。就在
这个时候,潘义说不行,这是六月一日,潘义说,“我们现在不能撤了,因为现在已经作
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坚持到二十日人大常委会的召开。要是在二十日之前你办起来,你
起码可以讲半个月的课。这半个月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然后撤退以后回到学
校再办。”我接受他的这个建议,这个建议非常好。当时就想要办,继续筹备就让人去做
舞台。可这个舞台让我等了两天,我已经失去希望了。第一天他说给我办了,第二天又说
人家很为难,第三天说联系不到汽车,因为舞台相当大。当时我想没问题,因为民主女神
都能拉来,大舞台当然能拉来。这时候因为这个就没有办成。
【 封从德:在设计民主大学的时候是否受到邱延亮的影响?
张伯笠:不是邱延亮,是潘义。我跟邱延亮没谈过民主大学,但是潘义跟我说,这是
邱延亮的想法。 封从德:在成立民主大学的时候,请教授为什么没有包遵信?
张伯笠:有包遵信。还有柴玲、王丹、吾尔开希、超华、李禄等等……
王超华:我在六月一日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个图,是关于民主大学布置的图。
张伯笠:我们五月二十八日就把这个图画好了。我解释一下,其中有一些国内的教授
不是我亲自同他谈的,比如刘再复说,“谁谁谁,这个著名教授我可以替他担保。”他实
际上没有接到我的聘请。
李禄:邱延亮在香港请了十几位教授。】
5.1.2 开学典礼
到了六月三日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镇压,我说,今天一定要办起来了,不要他那个
舞台了。拿着联络图按照位置是在这个民主女神像前面,因为那都是外地的学生,外地学
生就很愤怒,“我们的帐棚你们给我们挪了是不行的。”那时候是无政府主义,谁说也不
行,管你是张伯笠,是副总指挥。那怎么办呢,就挪到了民主女神像的东侧。我当时首先
告诉他们搭帐蓬,我们搭了八、九个红色的帐棚,整个形式都非常好,还搭了个大帐篷放
广播台。那么这个舞台怎么解决呢?因为要讲台呀。于是我就找法大的同学联系,他们有
一些桌子。我说,“你们能不能把桌子借给我。”他说,“借桌子可以,可是你们广场上
这些人不给我饭吃,不给我面包,我还能给你桌子?”我说,“这个不是我负责,你可以
找后勤部,找王钢。我搞宣传,我只能给你传单,不能给你面包。”后来他说,“你把学
生证押我这儿,我就给你。”我说,“我这个学生证不能给你。”但是我这儿有个牌儿,
上面写着副总指挥,他说,“那你得把这个给我。你必须把桌子还给我,才能取这个。”
我想,这也行,这东西不是很重要,就给了他。要不然这个桌子还是借不来。大概是弄了
七个桌子,就搭上了一个简单的讲台。
师大的项俊当时作教务长,赵世民是副校长。我就安排程序,起草民主大学开学典礼
的致词。这个致词大概是一千两百多字,改了多少稿,是很精炼了。当时设计的就是首先
剪彩,然后是各方代表讲话,我致开学典礼致词,第一课陈鼓应。可是陈鼓应在医院,他
心脏病复发,那天他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不能赴约了。我想可能他知道要镇压了。那么这
第一课就忙了,我说必须严家其来讲,他来上第一课。派了三个人打电话找严家其,找了
三次找不来,我一看已经九点了,我说现在就开。可那边呢?就已经接到了开枪的消息。
王燕就在广播里喊,说:“现在,”她喊得有点蒙了,其实是“民主大学要开学,希望大
家到民主大学参加开学典礼。”她说成了,“现在民主大学号召大家都离开广场去堵军车
。”我当时气愤得不行,而且她还喊“校长张伯笠号召大家都去堵军车。”应该是封从德
号召大家去堵军车,而不是我。我说,“大家不要去堵军车,大家要坚守广场,应该到民
主大学这儿来坐好。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继续开学。”
后来推迟到十点钟,才正式开始。这时严家其还没有到,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柴玲来
了。我说,好啊,严家其没到,咱们哥儿剪彩吧。当时非常正式,买了几百米的红绸子,
花了很多钱,这么大大的花。用新剪子剪开以后,我们俩就举了起来,然后就掌声雷动,
民主大学就正式揭开了开学典礼。当时有一万人左右吧。当时用麻绳拉了屋子这么大地方
,不让人进来。当时的人非常遵守秩序,那个地方是给记者留的,没有一个人进来,全坐
的是记者,但是很多不是记者拿照相机的也可以坐进来。
然后我就宣布了开学,中共喇叭再次打开,就是“民主大学现在又宣告成立。我们现
在再次警告你,你们要负法律责任,因为没有经过国家教委批准。”后来我就上去了,我
就讲了那一番话,地下就哄堂大笑,很高兴,给我热烈鼓掌。柴玲代表指挥部致贺词,马
少方代表大学生致贺词。我在美国华盛顿听说他的重要的罪证就是给民主大学致贺词,对
他宣判三年。老木代表知识界联席会议致贺词,赵瑜代表了作家致贺词。严家其这时候和
高皋到了。我非常高兴,我就说,“下面请我们的名誉校长给我们上第一课。”严家其讲
了大概有四十五分钟,他主要讲的就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含意和他对今后局
势的看法。他讲完以后就是民主论坛。民主论坛刚一结束,我重新上台宣布“民主大学开
幕式结束”的时候,军队就已经进了广场。一排一排的,我当时就是一种悲哀的感觉,我
们人民没有想到他们会开枪,是人民的愚昧、悲哀。当然民主大学就这样结束了。结束的
时候是十二点五十分。最后大概剩了有五千人。
5.2 撤与不撤 李禄
5.2.1 撤与不撤的争论
第一个内容就是撤与不撤的争论,这成为每一次广场议会的最重要的议题,有的时候
是第一个议题,有的时候是最后一个议题,每一次占的讨论时间都最多。我总结一下当时
两派讨论基本的理由。
主张撤的人理由是:第一,当时军队已经调入广场之后,这个运动基本上就失败了。
失败后要保存实力,要想把运动长期地开展下去只能撤离广场,只有撤离广场之后才能保
持学运火种,避免牺牲;第二,如果我们坚守广场,可为的事情不多,对下一步学运缺乏
明确的目标;第三,当时广场的秩序成为当时大家议论的中心,也是很多人同意撤离的原
因。
不同意的原因如下:第一,当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全国学运一个旗帜,这个观点主
要是由外地学生提出来的。如果在这边撤离,将使得各地的学运自生自灭,随后的秋后算
帐必然会到来,这对学运在各地的火种是一个打击而不是保护。而各地的情况,无论是群
众基础还是政府基础都远差于北京;第二,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已经齐聚到了广
场,他们在电视机前事实上是对于全体学生最好的保护。当时认为在全世界舆论的关注下
,中国政府还不至于做得太过分;第三, 按照中共以往的经验,既然他已经动了真格的了,
既然已经二十万军队调集到广场,当时不断地有各种各样不断升级的传闻,有一天传说是
导弹,而且有人照了照片来,后来发现那是毒瓦斯,认为镇压已经势在必行,不可避免。
如果我们撤离广场,之间的区别是这个镇压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当时认为秘密的屠杀
比镇压可能会更严重。当然这里还有没有说出来的原因,我想可以归纳成两个:一是对屠
杀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缺乏估计,当时认为最严重的可能是用刺刀、枪托,死人当然是会
死,学生领袖看来一个都活不成,但是对于大规模的用坦克、机枪的屠杀完全没有估计;
第二是有可能外地学生强烈地感觉到,出来之后都已经回不去了,在当地本校都已经上了
黑名单,回去就没有好果子吃。这是隐含的一个意义,没有讲出来的。
【 张伦:我问王超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有过一个会,这是当时在广场广播的,好多人
都去了。我想问的具体时间?这个会是怎么回事情?因为我的记忆里,在这个
会上第一次讨论广场撤退的问题。
王超华:我不能确认这个会的具体时间。我只记得,先开个会到各个学校去调查,群
众情绪都是希望撤。这应该是中午或上午的事。下午我们接着召集第一次代表
会,要求代表回校收集反应。第二次代表会,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张伦:高联最后作出决议撤出广场是什么时候?
王超华:高联没作出过决议要撤出广场。只是建议各校代表回校去收集反应,结果发
现这个决议根本作不出来。】
【 王超华: 五月二十三日之后退回北大,我们曾经几次到广场,包括我曾经在历史博物
馆旁边见到封从德、李禄他们去洗脸,其中提到高联负责外围,指挥部就负责
广场,而且封从德讲过,“我们现在很简单,我们就是等着他们来拖。”
封从德: 以静制动。】
5.2.2 指挥部的情报与对策。
六月一日晚上出现了第一次所谓的秘密情报。这里我补充一下辛苦这个人,他最重要
的活动是在广场以后。在辛苦之前情报收集制度已经建立,但是由于这个工作本身的秘密
性确实一直没有列在公开公布的各种指挥部运行的工作人员名单上,都是由我个人私下任
命的情报收集员,包括后来帮助指挥部和政府之间达成的几次见面,其实不是谈判了,这
些都是秘密的情报收集员作的工作。我们至少有三次和政府高级官员的会谈,但是开始的
联络都是我当时任命的情报收集员作的。辛苦最初成为情报收集员的时间,我不太清楚。
他说是由柴玲先任命的,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同学工作勤勤恳恳,而且特别可靠。当时情报
收集员的主要特征就是可靠,因为当时不需要你到外面去收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找你,
当然找的人也很多,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好几百个人,各种各样的情报也比较多,需要有
一些人把这些都整理出来。那么辛苦开始他自己首先做,每天晚上在我开联席会议之前,
他总是给我有时候是两页纸,有时候是四、五页纸的一个报告,就是他当天收集到的各种
各样的情报的总结,同时画图,按照当天情报定出来的军队的图等等。我就任命他作秘书
部下面的情报处处长。当然他后来作了其它的更多的工作,都是秘密工作,我就不再多说
,他自己也提到了。由他本人给了我一个十八省市的名单,将近四十多个人,包括他们的
联络代号等等。当然还有两三个同学作同样的工作,我就没跟辛苦谈。总之当时已经有想
法准备转移地下,这个工作就显得重要起来。
到了六月一日两三个信息同时传到,按照我当时的判断,好象都还可靠,军队已经准
备好要进城,当然对于进城之后的可能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一个很一致的报道,但很显然已
经比前几天得到的消息突然地程度严重起来,包括说是军队已经密集和外界隔断联系,已
经开到路口的军车已经腾空,已经没有军人在里面,军人自己整顿起来,这些消息都已经
被核实。所以六月一日晚上我全天没离开,本来每天还有两三个小时可以睡觉。尤其是那
天早晨刚刚经历了柴玲的绑架事件,当时指挥部对这个事件反应非常激烈,也是由于气候
突然转变造成的。我们当时确实有根据证明至少万朝晖这个人是和政府有关系的,这个消
息是我们见到一个中共高级官员在谈话中无意提出的,恰好就在那次见面证实万朝晖在这
个旅馆中同时有自己的一个套房。到了六月二日情况确实变得非常严重了,那天整个晚上
我从大概八九点钟开始就每几分钟就收到新的进展,我有两个人专门坐在旁边绘制一张图
,每过几分钟图上就有些变化,当时陪这我整个一晚上的是潘义。
当时主要作出的反应就是把帐篷里的人集中起来,这时候帐蓬已经开始建起来了,至
少一半的人已经转入了新的聚居地,而新的聚居地已经考虑了对付军队进城的办法,所以
这部分人是很容易集中起来。每个帐蓬设置了一个棚长,这个棚长迅速待命,当时政策推
行部已经建立,这些命令能迅速地传达到当时的每一个人,那几天晚上我相信所有的人都
没有睡好觉,都在等待发生意外。同时那天晚上和北高联开始有很好的合作,至少开希、
杨涛等人从那天晚上从师大和北大调进来将近一两万人。
第二天上午大量处理的是大量被捕的军人。当时被捕的军人很多,还缴了很多械。但
是这个情况已经引起了我们严重的关注,认为这是一场大行动的先兆。首先我们派出了政
策推行部的几乎全部人马去到各个被软禁的军人,说服同学把他们放走,同时询问到底发
生了什么情况。这时有两位中校主动向我们说明背后的意图,还有一名将军。按照这次谈
话的结果我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看法,这是一次预演,这是一次故意的疲惫战。气氛
开始被弄得越来越激烈,好象有一触即发之感。这时就有了武器收缴,把所有的东西都收
缴到指挥部。我印象里战利品还真不少,破枪破炮子弹一大堆,大部分是钢盔之类的,请
专家看了看没有一样开得动,刀子也生锈,枪也没枪拴。总之,这个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
显,这是一场故意的阴谋。
根据当时这些判断,立刻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公安局,从公安局里拿到了收条,召开了
三次记者招待会,向各位记者不断地展示收条,同时请政策推行部的人到各个帐棚去请棚
长和每个同学说明这一两天发生的紧急情况,请大家做好意外时刻的准备。当时的准备也
并不很多,建立的基本原则是五月十九日晚上到二十日晚上建立的所谓的原则,就是打不
还手,骂不还口,男同学保护女同学,互相并肩和平撤退,同时围成一个圆圈,这是接受
了一个空军少校的建议,叫中心开花,中心突破,学习了很多军事术语,最后形成了这一
套方案。这套方案在绝食最初的几天,每天都向大家传述,同时和医药站的人紧急商量弄
了几千个口罩和毛巾,为防瓦斯。后来这都发下去了,在撤退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至少有
一个毛巾或者有一个口罩。这是当时作出的一些反应。
到了六月二日晚上再次传出军队要强行进军的消息,整个晚上又是不眠之夜。这时我
对柴玲和封从德特别有意见,因为我在这时看不到他们,那个时候张伯笠全力以赴已经把
这个指挥部弄到别处去了,那时我感觉最欣慰的是潘义总陪着我在那儿,多少有一点温暖
。刚结婚的妻子早已经跑了。
【 柴玲: 绑架事件发生后,我的纠察们就把我保护起来,连李禄也找不到我们。】
5.2.3 屠杀就要到来
真正到了关头的时候是六月三日,这时所有的人到位了,所有的人都相信一场屠杀就
要到来了,除了张伯笠,张伯笠那个时候一心要成立民主大学。到六月二日半夜后我们全
都在一起,谁都没有睡觉,反复地商量。因为当天下午,跟北京市公安局的交涉,六月一
日的时候沈银汉的事已经是最初的信号了。那个时候整整一夜讨论意外事件出现怎么办,
这是六月二日晚上。那时军事物品还是不断地往这边带,还不断地有人带军人进来。我记
得那时辛苦已经是象猴子一样上窜下跳,一会儿就报告回来情况,我对他的情报已经完全
不信任了,他那个情报真是瞎说八道,那个时候已经不很平稳了。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人
都已经不平稳了。情况变得越来越危急,我的身体也觉得越来越疲惫,但是没有办法,大
家坐在那,大家吵架的时候我只能坐在中间。
到了六月三日上午的时候,情况突然变得火药味十足,主要是三个事件。一个是六月
二日晚上这个交通案,主要是柴玲和她的一大堆十几个助手在处理。但是中午的时候就出
现了所谓六部口事件,下午的情况我已经开始坐不住了,所以我就到各处去视察,主要是
在六部口地区视察。当时我的感觉是整个北京市的气氛已经很不正常,所有的市民变得异
常的暴躁、激动、愤怒,当时在六部口附近围绕了至少几万人,整个长安街全部堵满人,
我花了很大的劲儿才挤进去,那个时候六部口事件已经结束,但是弥漫着瓦斯、硝烟。回
来之后向柴玲报告,我说情况基本结束,好象不会再出问题,因为那时每天都出问题,六
部口一出问题我们就觉得又要出问题了。我说至少在我看来,军队在白天进入的可性不大
。但是情况变得很危急,接着就出现了人民大会堂西门事件。到了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
又传出小女孩被砸死事件,开始有人带着血就回来指挥部。晚上六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
我基本上确定一场大规模的、有预谋的、有组织的,可能会很残酷的镇压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我对残酷性还没有充分地估计。
我和柴玲决定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同时我们有一个协议,号召所有的记者都留
在天安门广场作这样一次大规模镇压的见证人,告诉整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印象
里当时柴玲找了一大批人去找记者,找到的外国记者很少,中国记者还是不少,最后,大
概有三十多个人。那是在纪念碑的南侧,由我主持搞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在这中间又有一个插曲,就是开希突然又开始精神抖擞到指挥部来向柴玲要求他要代
理总指挥,记者招待会他也去了。在那个会上我开始起草了指挥部最后一份通告,我当时
作了很多口头的以指挥部的名义作的宣言,我自己特别懒,不愿意写东西,所以什么也没
有留下,其实那些都是我口头讲的,后来不知道是谁记录下来了,总之那个时候已经开始
提出“打倒李鹏伪政权”,向大家出示了关于交通事件的报告,关于六部口的报告,关于
大会堂的报告,公安局送枪的报告,证据,收条。开希也来要求讲话,我们出于不是对他
的尊重,主要是怕他捣乱,所以每次开希来他想说,我都让他说。他就在那儿发表了一番
演讲,但当时我对他那个发表的演讲印象极好,那是我为数极少的对开希印象极好的次数
之一,他那天讲得很好。因为他当时也号召所有的人和学生站在一起,尤其是记者作历史
的见证人,这点我觉得特别合我的心意。当时在记者会上作证的还有两位在六部口和人民
大会堂受伤的工人,其中有一位是那个著名的拿着钢盔的,他的照片到处都是的那个人,
他也到那儿去作证。还有一个人我记得是推着平板车,受伤去作证,总之,这个招待会开
了有两个小时。
到八点钟结束我们回到广场指挥部时候,我们把我口头起草的议案又重新讲了一遍,
开了最后一次各校棚长会议,作出了“紧急待命,不许睡觉,准备好毛巾,同时向中心聚
集”等等。
5.2.4 六三这一夜
到了晚上九点有了第一个报道,在木樨地打死人了。在这个过程中,开希在记者招待
会结束后就随着我们到了指挥部,这个时候正式要求六小时指挥权。当时柴玲和我都分别
问了他,“你作总指挥有什么打算?”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时出现了第一例关于死
亡的报道,还说是个女孩,然后吾尔开希很激动拿起话筒来要讲,讲到这个女孩死的时候
,讲得很激动突然晕倒。我记得王童一笑,拿着广播说,“救护车,救护车,吾尔开希又
晕倒了。”那个“又”拖了有一分钟,旁边的纠察队员听说之后连捧带架就把开希带出去
了,以后再也没见到他,我就不知道他到哪去了。我的印象他每到这个时候一定要晕倒,
所以也没有出我们的意料,反而指挥部安静了很多。
安静的时间持续得很短,就开始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这时就作出了一个决议,
所有的人员立刻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手挽手肩并肩,帐棚里不允许留任何人。同时我
派出一些人,请所有的人都回来,不要再去堵军车,因为在这个时候关于屠杀的报道已经
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张伯笠让我去演讲,我不去,结果柴玲去了。
柴玲回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危急,那个时候至少围了有几十个人,有拿刺刀的,
有拿枪的。有人拿着枪对着柴玲说,“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
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宣布我当总指挥。”柴玲还没表示任何
说法,那边已经把刀捅到了后腰上,不仅是杨朝辉,杨只是其中之一,说“这么多人已经
都死在那儿了,你要是还让人死在这儿,你就要作历史的罪人。我要为这些人的生命负责
,如果你还不下令撤退,我先宰了你,然后我下令。”
总之情况就已经变得这么危急。而且这个时候伤员多得不得了,每个人都血糊啦喳的。
想通知开会什么人也找不着,各种表决也不清楚,而且情报部长也找不着了,总之已经不
再履行职责。谁也不知道军队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什么消息也没有了,只知道军队在三个
方向向天安门广场进军,而且在途中遇人就杀,遇人就砍,也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就到
了广场。对于各种各样的判断已经没有办法作出,如果撤的话,撤到哪条街道上?哪条街
道是生路?因为当时的感觉就象在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进村以后,把村子包围了一样,
哪条道路都出不去,出去就杀,反而呆在家里还有一线希望。所以我当时的基本想法,就
是在那时力图保持一个镇定的状态,当时我的基本想法是以静待动,我先把广场成为最和
平、最安详的一块地方,让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要死大家就死在一起,要没有死的话
还有可能保留一个生的机会。
在这个时候, 封从德就说了,“我们撤到纪念碑上去,我去那边安一个广播站,”这
时候封从德就转移到了纪念碑三层。从纪念碑三层到撤离这个情况,封从德最清楚。我最
后只证明一下,从那个时候起,封从德就一直作了最后的主持,那个时候我和柴玲在下面
的指挥部钳制大部分的人,因为他们来就是瞎捣乱,我们在那坐着,至少可以钳制这批人
,给封从德一个机会,在那边重新建立一个指挥部。后来就是这个指挥部保留了最后五千
人的生命,最后把他们带出广场。
我最后再说一句话, 关于这一段的报道实在太少。唯一有一次报道是杨涛*写了一篇
非常生动的文章(《民主中国》第二期, 1990.4),但是我对于杨涛*是否在场表示极大
怀疑。尤其是中间对于柴玲、我、封从德的描述我觉得实在与事实相差太远,在这里作一
说明。
【 5.3 屠城见证 李兰菊
我就讲从六月三日晚上十点钟到六月四日下午四点钟这段时间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大概是六月三日晚上十点钟,我跟香港学联三个代表,就是我、林耀强、陈清华,打
算到天安门去看一看,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已经杀人了。我们一下北京饭店的大厅,一
些香港记者就马上挡住我们的去路,说:你们不许出去,因为外面已经传出来杀人了,你
们一定要回去。我们没有说话,就回到我们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就跟香港学联通了一次电
话,香港学联给我们的答复,也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不许出去。后来我们四个人想了
一想,每一个人看了对方一眼就知道,都在笑,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出去,不能不出
去。所以我们最后就由林耀强起草一封信传真给香港学联:这一天晚上我们不代表香港学
联,只代表我们自己。然后就说:以后的就不用香港学联给我们负责,对不起要违抗你们
的决议。签了名就传真回香港。以后我们再给家人打了个电话,大概是十点半,我们就出
去。因为那个时候记者已经不在了,我们就很顺利地离开了北京饭店。
我们本来是要先到广场去看一看,然后就找一些纠察队。因为我们知道一些纠察队已
经出去挡军队了,我们就找到广场去。那个时候我们发觉广场上的人很少,平常有什么风
吹草动都有很多人在,可是那天晚上人不多,只有几万人,还有一些外地的学生在那里坐
着。那个时候情况也不是太乱。后来我们觉得当时在广场没有用,同学都出去挡军队了,
我们就觉得要跟着他们去。到了广场以后,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都不见了。林耀强就说:
我们到郊区去,他们一定在那里。我们觉得既然要去参加纠察队挡军队那个工作,可能回
不来了,所以我们就去指挥部先见几个朋友。好不容易我们进了指挥部,看见了柴玲、封
从德跟李禄。然后就是见到马少方,最后是开希、程真。后来程真还跟我们在一起,整个
晚上都跟我们在一起。最后见到开希,见了开希我们还觉得没什么,还在拍照。那张照刚
拍完,广播台就有一个同学在哭泣说:我们的同学都被警察开枪了,我身上都是血什么的
。开希就很激动,就进广播站去说话。
我们就离开指挥部,打算去追纠察队。那个时候大概是十二点多钟吧。(刘燕插:不
到阒樱坏恪3陶娓忝且黄鹱叩摹#┒浴4蟾盼颐亲叩匠ぐ步值氖焙颍涣咀?
甲车就冲过来,冲进长安街。很多市民,还有学生就要去挡它,有的是追它,有的是用石
头打那个装甲车,可是它就是乱冲乱撞的。我们当时也不知怎么办,因为很多同学已经武
装起来了。所谓武装起来就是有一些人拿着瓶子,有一些人拿着木棍、木条,还有铁条什
么的。我们觉得这事好象已经失去了和平请愿的那个方式,我们几个人就商量要不然我们
就四个人坐在长安街,号召人群用人墙挡那装甲车。我们那个时候仍然很天真地觉得用人
墙可以顶住那些装甲车进广场。可是我们看看旁边有很多人都坐在那里,在讨论局势。林
耀强就说:你现在坐下来人家也可能当你在讨论什么事情,没有用。我们还是去追纠察队
吧。
然后大概是凌晨十二点多吧,我们在长安街上跟着那些市民,也帮他们的忙,拉旁边
那些栏杆来挡着那些车子进城。大概是一点钟经过历史博物馆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看见
很多军人拿着很长的棍子出来,大概是一千多人。我们吓了一跳,军队真的进了城,他们
都是从地下上来的。我们在历史博物馆附近,人不多大概也不够三十个人,我们就马上组
成人墙,就坐在地上。那些军人有的拿着枪,有的没有,可是他们都很平静,前面的坐在
台阶上,后面二排的是站着的,再后面也是站着的。在历史博物馆前面,那个人墙跟军人
的距离大概是半个足球场,很远,真的很远。那时候程真带着我们唱歌,喊口号。当时我
记得旁边有一个小孩,十多岁吧,还在看小说。我说:你还在看小说,你还有心情看吗?
他说:军队不会杀人,不怕。一些工人还在维持秩序,还有一些工人看见一些学生或者是
学生看见工人拿着武器,他们都大声叫:听指挥部的话,和平请愿,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大概是一点多,信号弹就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放起来了。我记得大概是十五分钟以后,
历史博物馆后面就有枪声,最初的时候是比较慢的,比较疏的。后来大概是再过十分钟就
是很强。这些枪声响了大概也是十多分钟吧,我们就开始看见一些学生抬着市民重伤的一
些,或者是市民抬着重伤的学生,就是抬着一些死伤者从博物馆的后面走到我们旁边,他
们就抬着那尸体呀,受伤的人到我们旁边的一个救生站。有的就是把一些重伤的人用自行
车、木头车或者是汽车送到医院去,有的就放在那个救生站里边。那个时候我估计,包括
抬着走的,还有送到车上的,或者是在那个救伤站里面的,我相信死掉的起码有五个,受
伤的、重伤的超过十五个。我还记得有一个抬着到救生站去的一个学生,我肯定他是学生
,他在后面不知是给枪开了还是给棍子打了,看不清,全部都是血,都破了,他整个下身
都不能动,就是头在摇。他说:“你们看见啦,你们看见啦,你们都看见了吗?”这时他
就哭了。然后就说:“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可以放弃。”我也真的记不清楚那个时
间,大概就在一点钟到三点多钟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是一些军人,很多人都喊起来了。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有很多市民在追一
些军人在打。那个军官还是很平静,就是不让他的军队动。然后就是一些学生去救那些军
人。给打的军人大概是有四、五个,当他们看见学生去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停止了叫喊
。军队也有因为一些军人没有脱离市民的包围而继续叫喊,他们坐在台阶上,他们的军官
不许他们动,他们的情绪也很激动,就是喊,叫。他们见到一些军人给市民追着打,他们
就很激动。后来看见那些学生去救那些军人,他们就坐下来,就不喊了。这样的情况出现
了四、五次。
后来,我们三十多个人继续坐在博物馆的前面。突然之间有一个小孩,我看他不超过
十岁,也是从那方面走过来,我刚才讲的历史博物馆的后面走过来。他一边走就一边叫,
看见那些军人在历史博物馆前面,他就要冲过去。我就把他抱着,把他拉着不许他动。他
就大叫起来,和疯了一样。他说:“我哥哥给他们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我要跟他们
拚了!”他哭得很厉害,我就拚死命地拉住他,然后几个人来帮我的忙。他就老是在喊:
“我的哥哥给他们打死了!”后来他挣脱了我,跟着一辆离开广场的救伤车后面,一边跑,
一边喊。
这个时候我很激动,不知道怎么样好,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有一些人真的死掉了,军
队真的向一些学生们,向一些市民开枪。这个时候我看见有两个好象是青年女工,总觉得
她们不是学生,她们越过我们的人墙,走到那些军人去,她们要拉那个军官出来谈话,可
是给那些士兵挡住,他们就乱起来。我就趁这个乱的时间冲过去,拉着那个军官的手,就
跟他讲话,(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没有理智),我就告诉他们:“你不能向天安门广场的学
生开枪。我是香港的学生,我一直都知道他们是和平请愿的。你一定不可以向他们开枪。
”我记得我说了很多的话,后来我哭了。我看见那个军官也哭了,他的眼泪掉下来了。我
看见他哭,我就哭得更厉害,就跪在地上。后来林耀强他们把我抬回去,我们本来是坐在
历史博物馆的前面。我一个同学陈清华说:那边可能有事情发生了。他就要去看一看。大
概是十分钟以后他回来了,他的照相机不见了,人也好象给军人打过一样。他说他看见一
些市民在烧坦克,他就拍照,拍照的时候就给一些军人打了,照相机也打碎了。这个时候
林耀强跟程真也去看,他们不许我动,就要我等他们回来。
大概是两点钟,就剩下我跟陈清华两个人在历史博物馆前面的那个人墙。到两点钟三
十分左右,枪声越来越密,就是越来越近了。旁边很多的学生,很多工人已经拿起了武器
,有几个老工人一边在哭,一边在喊:“听学生的话,听指挥部的话,放下你们的武器,
我们是和平请愿。听学生的话。”就在叫,因为有很多工人已经拿起武器来了。后来他们
看见受伤的人越来越多,几个老工人也在喃喃说话,就是喃喃自语的,已经不在看,就在
马路边上哭。
这个时候我感觉很不舒服,好象要晕过去一样。那些同学看见我这样就把我送到旁边
的救生站去。救生站里边我看见很多受伤的市民和学生,那个时候在救生站里面大概有七
八个,被同学扶到救生站去的受伤军人大概有三、四个。七八个是受伤的,死掉的我不知
道。因为那个救伤站不停地有救生车来送伤员去医院,所以人数不多。可是他们一直都没
有送军人。我起初以为他们不愿意送军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为了这些军人的安全才不
送这些军人到医院去。后来枪声越来越近。这时来了一辆救生车,那些医生,还有旁边的
一些市民知道我们两个是香港学联的,虽然我们都没有受伤,可是救生车一来,他们就说
:香港学联的上车,上车。我跟陈清华拒绝上车,说:“我们没事,不用去医院。”受伤
的同学很多,我觉得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占用救生车的位子。后来来了两辆救生车,我们
都拒绝了。到第三部来的时候,一个女医生拉着我的手,她用英文跟我讲:“ My child,
you must get on the ambulance, we need you go back to Hongkong and tell the
world what had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 our government had done to us.”
她讲完就哭了。我就跟陈清华一起到车上去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到医院,因为途中有
很多市民,还有学生来挡我们的车。我们一边走,救生车里的同学一边用喇叭喊:“是学
生的车,不是军人的。我们不会救军人的。”原来他们沿途在堵这些救生车,他们不许学
生救军人。其中有很多都是女的,还有一些老太太。我要强调的是年轻工人、学生不多,
堵这些救生车的都是些老人家和女的。
后来我们到北京医院。救生车门一开,就看见医院根本就象屠场一样,到处都是血,
来接我们的医生、护士身上都是血,就是来推我的那辆车,也都是血。到了医院,有些医
生听说我们是香港学联的,马上就来看我们。那个医生是个年纪很大的,我觉得他是比较
高级的医生,他就马上来看我,我说“我没有事,我真的没有事。你去救其他的人。”他
跟我讲,“你没有事就好。你好好记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赶快回去香港。”
因为医院里这些人都很忙,我就没有到处去看,就在一层楼的走廊里面。只是一层楼
的走廊里面,起码有二十个受了重伤的人,有学生,有很年轻的,也有中年的,是学生还
是市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受重伤的人。其中有一个刚送进来,是另外一辆车送进来的
,他送进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一个护士上去把他衣服剪开,一剪开的时候,护士自己
也后退了二步。那个护士给吓怕了,原来那个人的胸口有一个饭碗一般大的洞,这个人不
能救了。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政权是用了达姆弹来杀市民的,来打那些没有武器的人。
那天晚上,我被安排在医院地下室的其中一个房间里,他们不许我们乱跑,就让我们
在一个房间里休息。其实我们很惭愧,因为地上全是受伤者,他们没有一个好好的休息的
地方,有的躺在椅子上,或者在地上。可是他们坚持要我们这样,一个护士说:“你们不
要再给我们带来麻烦,好好地在这里坐着。”所以整个晚上,我们都不敢出去。到了凌晨
的时候,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要出去看看。在我休息的房间旁边,也有一个小的房间,那
个房间里睡着三个很重伤的人。其中有一个我看他刚醒过来,他的面容好象很痛苦一样,
我就跟他说话。他很年轻,好象才十五、六岁,个子很小,我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小陶。”我没问清楚他全名叫什么,他只告诉我他叫小陶,我也不知道是
哪个“陶”。他说:“我是跟着北大的人去挡军队。”我问他,要不要我带个口信给你爸
爸、妈妈。他就说:“千万不要。因为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的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
,他们受不了的。请你千万不要给他们带这个口信。”然后我问他:你怎么样?因为我看
见他整条腿都断了,包着纱布,身上也是包着纱布。我问他你怎么了,他很辛苦地说:“
也没什么,腿断了,胸口吃了二颗子弹。医生说我没问题,可是我知道,我真的活不了多
少天”。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管哭,他反而安慰我,“你别哭。”他因为看
见我的香港学联的卡片,他说:“你是从香港来的吗?回去香港……”,对不起,我一定
要把他的话说出来,他说“你别哭,你是从香港来的吗?你别哭,你要回到香港去,告诉
全世界的人,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来帮颐牵镂颐恰!本褪钦庋:罄次姨档煤苄量?
,我就不再问他了。
我刚离开那个小房间不多久,有一个很年轻的医生进来。我们逗留的那个地方,是医
生和护士休息的地方,有几个护士在那里坐着休息。一个年轻的医生进来就哭,他哭着说:
“他们疯了,疯了,他们全都疯了。”那些护士问他怎么了,他说派出去的几个人都给他
们杀了,没有血怎么救人。那个年轻的医生就坐在那里跟护士们哭着发脾气。后来有一个
老太太,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医生,她就下来命令我们所有的学生说,“你们要马上走。
”那个时候已经是黎明快要天亮了,那个老太太进来就说,“所有的学生可以走的就马上
要走。因为我们接到的消息,军队就要进来抓人了。”就要我们走。
我们跟陈清华就打电话给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说:“对不起,我们管不了。你们
就留在你们现在的地方。”我们问可不可以给我们一辆车,他们回答:“没有可以用的车
。你们就留在你们现在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他,我们只能想办法,看能不能跟
我们的同学联系。
这个时候,我们想在走之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们恐怕我们也会被那些军队抓去。所以
我们就在我们的名片上,写了“香港学生李兰菊、陈庆华被抓了。请马上通知海外记者。
”这句话,大约写了十多张。我们原定是如果被抓就偷偷掉在地上,让人们发现。后来我
们回到香港以后,西安电视台播送新闻说:“香港学生陈清华、李兰菊到处造谣撒谎,攻
击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另外,我的包里面有梁二交给我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就是他临走之前,他说他恐
怕有危险,就把包里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一些学生的名单、地址,很多很多你们开会的
议程都在里面。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商量该怎么办,我们就怕我们被逮捕以后,这些文件
可以拿来作为证物去起诉或去抓一些同学。我们想了半天,决定把这些文件烧掉。可是那
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就求他们让我们出去,因为在地下室没有地方可以销掉文件。后
来有一个护士带我们到厨房里面去,我们就告诉那些厨师,告诉他们这些事情。他们就说
,都拿来,都烧掉,看他们还凭什么抓人。这样把那些文件都销掉了,梁二知道后一定会
很生我的气。
六月四日中午时分,我们已经通过电话联络到李卓仁。李卓仁说他来接我们。因为他
比较了解外面的情况,他劝我们不要冒险,他来接我们。我们知道可以走了,我和陈清华
每人身上大概有二千元人民币,我们就把这些钱分给医院里面所有那些可以走得动的工人
、学生,都分给他们。因为我们走动的范围不多,我们不能把钱都分了,所以就把剩下一
千多人民币交给医院一个年轻的医生,请他看见那些要逃亡的学生或工人就把钱给他们。
然后就在下午四点钟离开医院,离开医院以后,回到旅馆。
六月五日下午,我们跟香港学联,还有十多个香港的学生和记者就回香港去了。
离开医院之前,我去那个小房间再看小陶一面,他已经死掉了。这是下午四点多钟的
时候,我不知道他死了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李兰菊的见证之后, 鉴于与会者情绪波动, 大会决定不再在会议期间作屠城见证,
建议大家各自写回忆文章。】
【 封从德:六四屠杀过后,你们在复兴们医院知道有二百四十具尸体,是怎么得到这个
消息的?
常劲:当时有一个高联副秘书长,我现在不愿意提他的名字,我们当时派一个记者到
各个医院,总共是四十多家北京市的医院去调查,因为当时有些我们学生是市红十字会的
联络成员,就在六月三日晚上,我们曾经给这四十多家医院打过电话,请求他们紧急动员
去救学生。调查以后,当时有很多数据拿上来,我没有仔细地看数据,我只看了一下复兴
门医院,因为是我们系的同学去调查的,说是二百四十多具尸体。 】
【 杨涛*:我补充在六三晚上我看到的学生死亡情况。在广场西北角有一个帐棚,是红 十字会医院的帐棚,在这个帐棚因为我有个老乡他在木樨地中弹。我陪他到这个帐蓬里治 疗的时候,我看到了在北长安街跟广场边缘地方军队一开始进来的时候跟学生冲突,纠察 队员向军队扔燃烧瓶,军队向纠察队员射击。我看到许多伤员、中弹的学生被医护人员救 理到,我看到一个学生他所有的内脏都翻出来了,把他放在下面的时候医生就围着他,过 了五分钟医生全部走开,一个医生从他的裤兜里掏出学生证放在他的脑袋上,然后就不管 他,去看其他轻伤的同学。我觉得很奇怪,我走近他,但是我不敢接触他。我问医生有没 有希望,他说,“你看有没有希望?”然后我就走了。】
5.4 撤离广场 封从德5.4.1 口头表决
六月三日下午两点钟, 新华门前催泪弹炸响时, 我正好在长安街要到林耀强住的北京
饭店去。然后他带着我去北大,去的原因就是香港同学建议由北高联再派两个副总指挥到
广场上来,这个事情我和柴玲、李禄都原则上同意,那么我们就想去请他们。到了北大看
见开希、梁二、程真,当时有个戏剧性的印象: 梁二骑着车,程真在前面,开希在后面,
搭着车在那儿玩儿,我觉得气氛和广场不一样。当时我的印象梁二是北高联的常委,所以
如果师大要出副总指挥的话,我只能请梁二来作副总指挥,这时开希就说,“我们师大是
主席负责制,我现在就宣布撤销梁二的常委,我来作。”这样开希就跟着我们到了广场。
到广场的时间是六、七点钟。当时我去北大还有一个原因, 是要组织一个新的纠察队。我
当时已经买了三百件北大的T恤——必须要有一套“制服”,有一种威慑力的队伍才能镇
得住广场的秩序。(删三段。)
晚上十二点到两点是转移财务部,最后我只领了五千块钱留给广场指挥部。广播站的
转移也是我来作的,直到凌晨两点钟。纪念碑当时的混乱情形刚才李禄已经很生动的描述
了。然后是四君子来劝退,我们开始都不太信服,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软骨病又犯了,
后来发现他们讲得还是比较有道理,而且感动了很多同学。这个时候就收枪,当时辛苦缴
了一挺重机枪就给砸了,收汽油瓶、收石头、收木棍,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你要是扔一
块出去,全场的同学都要跟着你全死掉”。这是当时非暴力的气氛。
侯德建去谈判,这里我再次要强调一点就是,他去谈判之前来征求过指挥部的意见,
当时至少我亲口对他讲,“你只能代表第三方,不能代表指挥部。而且指挥部也没有作撤
的决定的权力,权力在所有的同学。”所以李禄说,“这是最后的营地联席会议。”这不
是代表大会,而是直接大会。最后就变成了口头表决。我再分析一下作这个口头表决时的
心理状态。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广场已经被军人给封锁了;对当时屠杀的情形我知情;但是
没有很深的感觉。当时为什么要表决,我是认为经过四君子的劝说,人心已经动摇,那么
鉴于以前我的经历,担心同学逃散,在散的时候自己人踩死自己人,让中共拍下录像来,
看笑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口头表决的结果,我的印象是喊撤和喊留的声音一样大
。既然已经有一半的人想撤,我就担心这那种奔散的情况; 而且, 我还有一种心理判断,
认为喊撤的人不如喊留的人理直气壮,所以我相信想走的人更多。所以就这样宣布了撤。
最后指挥部的人和同学一块走的时候,我们离穿着迷彩服的军人, 不到五米。
【 谁砸机枪? 辛苦
在海外听到许多民运人士因为对一些细节的谈话来证实自己的身份,这样就可以进行 一些夸张。比如说象绝食四君子的行为,高新出来之后谈到一些情况,然后就对学生领袖 进行批评。有些批评是中肯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种误会,彼此之间的不理解。我最后就 想讲一件事实,就是刘晓波最后砸机枪,借此来证实他们理性和平的争取,这纯粹是胡扯 八道。这个机枪是我自己作的处理,我非常明白。那天晚上我已经累的,因为三天没有睡 觉,最后大概睡了三十分钟被我的保镖踢起来了,因为实在是叫不醒。我起来之后发觉我 的头下面硬硬的,我问是什么,他们说是机枪。我一听,开始还挺高兴,尽管我在晚上的 时候收缴了三批武器交给公安局。这个机枪我一检查没有枪拴,我说这玩意儿留着我们都 活不了命,又不敢抬下去,因为下面已经站满了军人。这个时候我就用我们那个小帐蓬, 是我跟李禄的那个小帐蓬里面的一个小被子把那个机枪裹起来,李禄的保镖,我的保镖和 我自己抬着到纪念碑南面下去直到毛主席纪念堂前,喊一二三,扔到花木丛里面。因为旁 边两边已经站了军警,我们害怕起误解活不了。具体时间是在三点四十分左右。 】
【 纪念碑上 梁二
六四前夕我和马少方从北京饭店出来,台湾电视上在当晚有一个台湾学生跟大陆学生
联欢的活动,马少方代表大陆学生致了词。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回到广场,然后我就看到
广场上秩序很混乱,我见到了李禄和辛苦,当时我不认得辛苦,我记得是有一个收枪的人
,所谓的纠察队长,有一大帮人在那儿。我当时要求进指挥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阻碍,但
是李禄见到了我们说,让马少方和梁二进来,我就进去了。当时李禄是盘腿静坐,柴玲在
哭泣。我当时问他,“你是否有所决定?”李禄说,“现在还没有任何决定。”我就说现
在当务之急是撤与不撤的问题,我和马少方就是希望有组织地撤。有一个同学进来谈到工
自联的问题,在旁边插话,我当时就想,工自联在外围。李禄说,“我们需要先进入到纪
念碑周围。”第二次进入之后,我又去追问的时候,李禄给我的答复是,“我们有必要把
同学聚集到纪念碑周围,再来考虑撤与不撤,先有组织地集体静坐在纪念碑周围。”我觉
得他的建议相当好,所以我马上就同意了。马上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一撤下来,工
自联就成为一个孤岛,我和马少方当时就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相互交谈之后,我记得当时
有潘义和李兰菊,我们一块到了工自联。我们与他们交涉的结果是,一个络腮胡子的人答
应,必要的时刻撤退下来。后来我得到一个工自联来的朋友给我的信息说,他们确实是撤
下来了。柴玲的录音当中我对她进行否证,就是工自联的人并不是全军覆没在那广场的西
北角上。我要证明这点。这个时候我实在找不到封从德,而且也找不到开希、邵江,找不
着其他的高联常委,所以我就到纪念碑的第三层去了。
在纪念碑第三层,我与马少方就遇到了程真。我就发现指挥部已经搬到第三层了,当
时是封从德和李兰菊、李禄,他们都在纪念碑第三层上面,林耀强也在那儿。林耀强是跟
我们一块走的。到底撤与不撤还是没有定性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和马少方提议我们作为
高联常委会代表,作为一度的学生组织者必须到广场的最前沿,我就跟马少方坐在最前沿
。
撤退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从我们的角度没看见任何在广场上的流血事件。在中间
的时候我们命令一部分师大的同学独自撤退,是我给他们探的路,带头的人是师大地理系
的同学和师大的一位老师,从广场的东北口出去的,当时我在那个地方探路时军队杀死人
的现象大约数目应该是三到六个之间。我和朝晖、马少方走在最后,出去之后,少方就独
自跑了。朝晖在这个时候被人踩住了,我把他拉出来,之后再找少方,他已经不见了。这
个时候我就与邵江、高新在一块了,这时碰到林耀强、程真,我们组织队伍撤退了。这里
我要对高新的一篇文章澄清一个事实,我是在六月四日上午十点才离开前门那个地区的。】
5.4.2 撤离之后 凌晨七点,到了白塔寺, 有四具尸体躺在十字路口,当中一具还在抽搐,我想去救,
因为我在前面开路,这时市民就冲过来要揍我,说这些人是军人,边上的护士都不救他,
说他们在那个地方杀了四十个人。西单的橱窗上写着: “这不是墨, 是人血”。(删八十
字。)
沿途, 同学们烧了很多挂起来的横幅什么的,特别是在西苑饭店,上面写着“坚决拥
护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然后到了中关村,最后到了北大筹委会,我们在二十八楼,就是沈彤那个屋子里边开
会,解散我们这个指挥部。分发那五千遣散费时,记得李禄和辛苦各自只要了二百元。我
当时在广播站向回来的四五百个外地同学宣布,他们的去向由北大筹委会接待,北大师生
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休息、隐藏的地方。
后来见到X,他最后一句话跟柴玲说,“柴玲, 你现在的名气很大; 你看着, 以后我
的名气会比你更大。”之前他建议我们去另外一个学校,说“我们在那里准备了几十本护
照,有很多知识分子,”我当时非常生气,一句话也没有说。(删八十字。)
我和柴玲发誓:一定要活下去!然后就是北大筹委会给我们五千块钱和一千外汇券,
我们从此开始十个月的逃亡。这十个月的逃亡,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来帮助,完全是帮
助我们的这些人自己成立了组织。没有任何海外的一分钱任何一个组织,唯一跟海外接触
就是给李禄写了一封秘密的联络信,但是一直没有回音。
【 常劲: 屠城以后北大做的主要工作是疏散的工作。当时广场上的学生有一部分退到北
大,全国各地的学生主要是集中在北大。北大同时还有很多自治机构的重要办公点,我们
就能发钱的发钱,能疏散的疏散。北大筹委会设想是转入地下,一个是我们分散到各地,
一个是重新进入合法的学生组织,进行掩护。在绝食后期我们就开始积累这方面资金,当
时北大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一笔活动经费,我们希望转入地下以后能继续保持北大筹委会的
活动能力。
北大筹委会从六月五日起就不再公开地作各种的反对和追悼活动,我们移权给治丧委
员会。治丧委员会是同学自发成立的,彭嵘纠集一帮人自发成立的组织。我们希望他能把
校园里的活动担当起来,北大筹委会主要是做疏散和内部的转移工作,当时就是这样的结
局。六月四日北大筹委会每个干部都有疏散费,有一千块钱的疏散费,柴玲和封从德到了
北大以后,我们同样给了他们疏散费。
六月四日以后北高联常委全部失踪,只剩下王有才、邵江。北大筹委会在没有征得高
联同意的情况下以高联的名义发布了许多消息,发了许多传单和公告。六月四日上午在北
大二十九楼前面设了一个高联的接待站,接待那些跟高联有联系的需要疏散的人。
北大在屠城以后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关于屠城事件的调查,当时北大联络了四十
多个医院,派了二百多个记者,到各个学校、各个医院去调查死亡人数。当时我确实知道
的北大的死亡人数,北大校方给我私下谈的是十四个。我自己因为当时负责很多的工作,
没仔细地看,调查结果,复兴门医院一个医院里就有二百四十具尸体,其它医院我就不知
道了,总共有四十多个医院。 梁二:就刚才常劲提的,从广场下来的高联常委的失踪。
六月四日中午十一点半我到达师大。这之前我曾经送杨朝晖从广场上撤下来,在十点
时进入红十字会的一个急救站。回到师大之后,遇到一个接待的同学,我就源源本本地谈
了我在广场上的所见所闻。之后,遇到马少方正好来找我。我对马少方说,我刚才打了很
多电话到各校筹委会,都没找饺恕>菟抵饕牧斓级汲妨恕8蘸糜幸桓龃硬ㄊ慷俅蚶吹?
电话,说他们在其它学校问了一些人,但都不是自治会的领导。我告诉他,我是刚从广场
撤下来的。讲了一下我的身份和在师大和北高联的职务。当时我觉得很气愤的是每一个人
都走了,而把我和少方留下。那天晚上,实际上我还骑车到过师大,发现人大和师大的广
播站在那天晚上都还开过,因为有一辆瓦斯车开到师大,要对师大的同学进行镇压的时候
广播才撤掉。
在这之后我发现,六月三日晚上一些很主要的领导者都已经退离广场。而且当时的决
策者好象还是抱着一种彷徨踌躅的态度,不敢作定论,表明撤与不撤。
李禄:
我退到北大的时候,当时看到王有才、常劲也在,这个我能证实。我下午二三点离开
的时候,他们还都在。六月六、七、八日的时候,我到北大去的时候就没人了。最后一次
见到的只有张智勇一个人,王有才已经不见了。他告诉过我,说他一定要坚守在北大的自
治会,代表高联发动全市人民抗暴斗争,要坚持到被捕为止。 】
【 杨涛*: 六四之后,我先在北大,后来辛苦找到我,把我带到李禄的住处,我们住在 一个知识分子的家里。后来李禄成立地下指挥部,李禄起草了《广场指挥部对时局的最后 声明》,我帮助记录。李禄在出逃前任命我为南下总特派员发展江浙学运,李禄口口声声 对我说,他到南方取经费,我就等他的经费,结果我等了十多天没有经费。李禄的通缉名 单出来以后,那个知识分子就劝我,“你也别等了,你逃吧。”我的家乡浙江省政府贴出 了一些到京参加学运的名单,到公安局报到,我是第二位,我就决定出逃。 】
【 李录: 刚才杨涛*提了一下,我任命他作江浙的地下运动的总联络人,当时我任命的 人可不只他一个,我任命了好多。很遗憾,这些人都在等我经费。问题是封从德没有给我 经费。 】
Back to Top
Forward | Note | Participants | 1 | 2 | 3 | 4 | 5 | 6 | 7 | Index
中文主页 | 关于影片 | 音像图库
| 民主墙 | 六四史料
| 网站导览 | English
©
Long Bow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