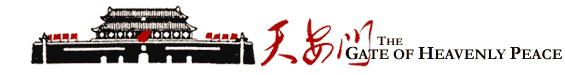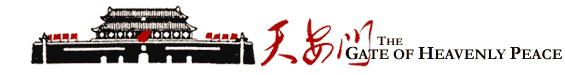关於天安门运动的三言两语
龚小夏
有些朋友希望我就最近民运中出现的一些争论,特别是有人在《北京之春》
上对我提出的批评作点回应。不巧的是,由於临近毕业,诸事繁忙,兼又搬了家,
我在最近数月里既没有收到、又没有时间去图书馆翻阅中文出版物,所以对事情的
前因後果不甚了了。为此,跑去匆匆翻了一下六月号的《北京之春》,才发现是因
为《纽约时报》和《世界日报》上有记者对柴玲女士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末的一次采
访中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提出了一点批评,因此在民运圈子内引起了轩然
大波。而我之所以被牵连进去,则是因为《联合报》记者薛晓光女士在写文章之前
曾经从香港打电话来就对柴玲的谈话的看法对我进行过采访。柴玲女士的讲话录音
,在此之前我曾经认真地听过,里面有许多逻辑全然混乱之处,而且往往语无伦次
,精神崩溃之征兆相当明显。因此当时我对薛女士表示,由於我研究的是社会学而
非病理学,所以我很难对柴玲女士本人的做法提出多少评论。但是,我希望就八九
年运动本身提出一点看法,亦即八九年的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但很难成
之为民主运动。另外,我表示不同意我的同事丁学良先生关於文革後一代人的意见
,因为在我看来,每一代人受不同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固然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但
是每一代人中都有一批富於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同时也都有那么些为一
己私利不惜牺牲天下人身家性命的极端自我中心份子。关於这点,我在《一般民运
,两般人物》一文(见《北京之春》九四年九月号)中已经阐述过了。
既然争论是由於柴玲女士的话引起的,而从目前的文章看,包括许多参与争
论的人也没有完全读过柴玲的采访记录,因此,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或误会的最好办
法,大约是请《北京之春》或另外哪家中文报纸杂志将柴玲那番话一字不差地刊登
出来,以便有个争论的根据。否则,无论人们就此发表什么样的意见,都难免遭到
“断章取义”的指责。
在《北京之春》上,似乎只有一位叫白梦的先生对我有所非议,所以看来我
也只能去回应一下这位我从未谋面的批评者了。然而,在读过白文之後,我却不知
从何回应起。这位作家班学员的写作生涯大约是从向组织打小报告开始,通篇对人
的指责包括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表现之类。他若有兴趣作进一步调查,尽
管可以去费时费力,我却没有兴趣对这种专案组审查结论式的东西发表什么意见。
等什么时候他能拿出比挖家庭出身、追个人历史、查社会关系这一套更新鲜有趣一
点的办法来时,没准作“回应”式的对话还能有些基础。
另外,由於我没有看过《天安门》一片,特意向卡玛女士提出过要求,希望
能借 来一观。殊不知,据卡玛女士说,由於该片还未完成,除了对极少数有关人员
放过一点样片之外,从未有人看过此片。这令我顿时哑然。不知道白梦先生根据什
么指责卡玛女士“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断章取义”、“歪曲历史”等等。
不过,这点与白先生的风格思路倒也算是统一。
关於白梦先生对我的指责,大概说这么些也算是足够了。不过,我倒想趁此
机会向包括白梦先生在内的一大批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说上几句肺腑之言。
柴玲女士那番如今引起争论的录音讲话,尽管有许多混乱和歇斯底里之处,
但在总体上反映了八九年运动中相当一大批学生领袖对投身反抗政府的运动没有任
何思想、理论、心理上的准备,甚至没有将自己看作是政治上的成年人的普遍状况
。正如柴玲在讲话中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学生领袖口口声声管示威的学生——包括
他们自己——叫“年轻的孩子们”。在运动特别是绝食的过程中,他们一再呼吁“
祖国”和“人民”来“救救你们的孩子”。的确,在政治中不作为成年人出现,一
方面固然是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同情,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容易能逃避运动的参与者
、尤其是领导者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学生领袖们作出这种不成熟的姿态,
似乎更多是由心理上的畏缩与思想上的空虚所引起的,而不是在政治上深思熟虑的
结果。
心理上的畏缩,并不是指这些学生领袖胆怯或怕死,那是另一个问题。心理
畏缩的表现,在於不愿意正视现实,不愿意面对现实中每个个人的责任、义务以及
运动所面临的来自各种情况、各个方面的威胁。与此同时,却一味追求戏剧性的效
果,并以夸张的话语及行动——例如声称要自焚之类——来掩盖自己的不负责任或
不敢负责任。结果是,最没有主见的人往往看起来最激进、最坚决,最感情用事的
人反而最容易成为领袖。当事情弄砸了之後,最应该负责却又最不愿意负责的那些
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最容易以一句“年轻”来将他们所有的责任搪塞过去。
这些学生领袖思想上的空虚比他们心理上的畏缩对运动产生了更多负面的影
响。他们受的是共产党教给他们的语言,唱的是共产党教给他们的歌曲,模仿的是
共产党树立的“英雄”形象。除了共产党教给他们的之外,他们自己掌握的思想武
器着实有限。毛泽东年轻时期创造下、由文革中的红卫兵大力宣扬的诸如“国家是
我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
谁干?”这样的语言竟然成了绝食学生的口号;而若是共产党的《国际歌》还有些
政治反抗意味的话,象《血染的风采》这样的歌曲竟然成为广场上学生们的“场歌
”之一,便令人觉得是运动的耻辱了。
思想上的空虚的最集中表现,是学生领袖们,特别是激进的学生领袖,在运
动中从来没有能够明白地解释抗议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与这个政府的关系到
底是什么?政府是他们的政治对手甚至敌人,亦或是他们的领导甚至保护人?学生
领袖们似乎从来不清楚。他们一时会管李鹏叫“人民的总理”,摆出一副臣民的姿
态在大会堂前下跪;一时又会表示要“推翻这个灭绝人性的政府”,并且拿出一副
与政府决一死战的样子。他们虽然痛骂政府专制,但是从他们的实际策略——如果
他们还算是有一点策略的话——中又实在看不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将政府的专制当
真。他们许多任性、不负责任的做法使人怀疑他们到底是否知道专制为何物。甚至
柴玲在痛哭流涕地声称“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的时候,她所给出的理由也不过是
“只有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事实上,专
制政府之第一要务,便是对反抗它的人进行残酷的镇压。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不是一
天两天的事,而天安门运动并不是发生在专制最严厉的时期,相反却是在专制相对
比较松弛的阶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社会稍微有一点点经验的人,用不着在
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景象,也能够知道共产党政权对反抗它的人从来就没有客气
过。因此恐怕需要擦亮眼睛的只有柴玲这样的人的眼睛。
思想上的空虚导致政治上的缺乏明确目标,而为了掩盖政治上的无所适从,
许多学生领袖便更倾向於不顾後果而采取激进的策略,不断地制造戏剧性事件,不
断地将所有解决问题的建议——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都斥责为阴谋。或者说,一
些人由於没有策略才采取了激进策略,因为拿不出办法来所以才拿出了最不妥协的
办法。而最终,运动的没有出路则成了某些人保持自己领袖地位的唯一出路,使得
他们对八九民运的悲剧负有不容推卸的个人责任。
如今,天安门运动过去六周年了,而当年那些总是以“年轻的孩子”自居的
学生领袖们也有不少人接近而立之年,再拿出一副孩子样来撒娇犯嗲,大概也不是
那么有趣了。是不是他们应该趁这个讨论的机会,重新来回顾他们自己做过的事情
呢?但愿他们能够如此。
这篇文章,是写给那些还愿意反省一下自己、检讨一下八九年运动的得失的
人们看的。如果有人嫌这里面缺少了溢美之辞,不够那么“一分为二”,尽管可以
去读别的东西。要是有人又嗅出了什么“反民运”的味道,想方设法去调查我的家
庭出身和个人历史,则请自便。本人工作太忙,恕不奉陪。□
原载《北京之春》
中文主页
| 关于影片 | 音像图库 | 民主墙
| 六四史料 | 网站导览
| English
©Long Bow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