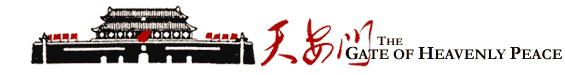 |
||||||
为什么《天安门》没有采访到柴玲?
——《天安门》中文稿本补记
卡玛
“天安门”影片中采用了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与美国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影讲话的许多片断,并成了日後有关影片争论的焦点之一。许多人问及柴玲作这个谈话时的背景,以及为什么影片中没有能采访到柴玲的原因,现特在此作一说明。
柴玲“5月28日谈话”是怎样录下来的?
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 原是密执安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专攻中国历史,1983年来到中国,一住多年,深入民间,以便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从1986年到1989年,他曾以制片助理和翻译的身份参与了数部有关中国的影片制作。“六四”之后,他把自己当时的经历详尽记录,终成一部书稿,名为《天安门之月》(待出版)。
1989年,当北京的抗议运动成为西方国家的“重头”新闻后,西方各大媒体的主播蜂拥而至,取代了较为了解中国情况、懂得中国话的原驻记者,成为西方观众了解中国事态发展的主要媒介。尽管当时的运动使外国媒体大员们眼花缭乱,摸不着头脑,但他们施展在多年商业新闻环境中所形成的个人魅力和包装技巧,选择和制作新闻时优先考虑的是必须有主播人亲临新闻所在地的现场气氛,必须在西方早新闻时间抢在其它电视台之前播出事态的新动向,被采访人必须能够操流利英文说出简短却又精彩的台词式语言,等等。这些包装一下使新闻的“可观性”大为提高。
当时的金培力就是在帮助BBC的这样一位主播安排采访。虽然他总想使报导能够比较深入、准确,然而他的努力往往被媒体大员们的上述种种技术性考虑所压倒。金培力注意到柴玲在广场指挥部的核心地位,当时一大群香港记者追着她,而她却极少接受采访。也许是由于金培力在北师大住过很长时间,而且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得到了柴玲的信任和采访许可。
据金培力回忆,5月26日,他带领BBC的大主播来到柴玲的帐篷,准备自己来作这个难得的采访。不料待摄像机架好,一切就绪时,不懂任何中文、也不知柴玲为何人的主播却让他靠边,要亲自采访。但一张口才发现不可能用英语和柴玲交流。于是大失所望,最后竟连人带机器一撤而空,留下柴、金二人面面相觑。金培力感到柴玲有一种需要理解和倾吐的欲望。几乎不用提问,柴玲就将运动一个多月来的经历和感受向金培力托盘而出,“如同要放下一付沉重的感情负担。”由于一学生进来向柴玲报告情况,打断了交谈。两人告别时,柴玲突然说:“我能够信任你一件事吗?我想逃走。”金培力惊讶不已,柴玲又说当下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听说英国使馆开始接受学生领袖政治避难,不知金能否替她打听这种传言是否可信。突然受此信任和重托,使金培力深感责任重大,但他也了解情况的复杂,深知冷静思考的重要。他建议柴玲提高警惕,小心这是政府设下的圈套,另外也要小心英美使馆会把她的避难作为政治筹码,不如进一个中立的小国使馆比较稳妥。金培力将自己在北京饭店的临时房间号码告诉了柴玲,以便日后联系。
两天之后,面色灰白憔悴、“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柴玲突然在北京饭店的大厅里找到了金培力。
“你能帮我吗?”她问。
“当然,”金培力答到,虽然他对这场运动有自己的各种分析和看法,但对于站在面前的处于困境之中的这位弱小却极为坚定的学生领袖充满了敬意和同情。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有事向你说,但这里不是地方。”柴玲紧张地说。
金培力于是招了辆出租汽车,刚要开动,一位多日来追着柴玲要求采访的香港女记者便一屁股坐进车里。金培力对她的不请自邀感到有些恼火,却也不便把她撵走。出租车在市区兜了几个圈之後,焦急之中的金培力忽然想起一个经商朋友的住处可能相对安全。于是几个人一同来到那里,还未坐定,柴玲便说:“警察在到处找我,我的名字已经在黑名单上。如果我被抓住,就会被判十五年。”金培力拿出一个随身带来的小录音机,女主人又找出了一架家庭式录像机,录下了柴玲与金培力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谈话结束后,屋里的人都被柴玲声泪俱下的表白所震动。为了避免柴玲在这种很激动的状态下会有某些表达欠妥的地方,金培力建议众人再把谈话从头开始看了一遍。当看到柴玲说出“我想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时,金培力很替柴玲担心。
“你觉得这样说行吗?你用的可是‘推翻政府’这几个字啊。”金培力提醒柴玲充分考虑公开讲这样的话会给她自己带来的危险后果,并问柴玲是否要把这句话从录影带中删掉。
“不用,就这么说。”柴玲镇定地说:“没关系,等这盘东西播出来时,我早已转入地下。”
柴玲给金培力写了一个委托书:
“也许是最后的话了。我要用生命来请求和委托 Philip Cunningham 向全球的华人转达我真实的思想和感受。
柴玲 89.5.28.”
受此重托,金培力即刻给驻京的几家美国电视台打电话。由于害怕电话被监听,他不愿透露自己和柴玲的名字,只询问各电视台是否对“一个重要学生领袖的采访”感兴趣。结果只有ABC表示了点兴趣。
据金培力回忆,他们休息片刻,金培力和那位香港女记者把柴玲送走,路上经过ABC在北京长城饭店的办事处,留下金培力的联系电话,以便转交录像磁带。然後,柴玲吩咐金培力去纪念碑上找封从德,以在离开北京前,再见上一面。
金培力陪着封从德到达约定的见面地点----前门肯德基炸鸡店,却没有找到柴玲。待金培力再一次见到柴玲时,她已改变主意要留下了。运动中的许许多多细节在金培力的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和评论。读者大概只有待该书出版後方可了解到全貌。
我最初看到柴玲“5月28日谈话”是在ABC夜间新闻主持人Ted
Koppel主持的“夜线”节目。1989年6月27日播出的“夜线”一小时专题报导中引用了那个谈话的几小段,并采访了金培力。后来我在为拍摄“天安门”而研究各种资料的过程中也不断看到被称为“柴玲谈话”或“柴玲文章”的文字,长短不一,内容近似,却又有出入,而且没有注明采访的时间、地点、及采访人姓名,无从考查,因此我认为都不能当作确凿的史料。直到1994年才辗转找到已旅居日本的金培力,看到了这次谈话的完整录像原版。据金培力说,他们后来根据录音带整理出了一份记录稿,发到香港。台湾所出《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收入的想必就是此稿最完整的版本。然而与原录像带对照,由于当时记录的时间仓促,录音带质量很差,记录稿仍有不少出入。
柴玲拒绝我的采访
拍摄“天安门”的工作一开始,我就一直希望采访到柴玲。1990年,当柴玲刚刚从国内逃亡到美国,在华盛顿参加各种会议时,我应全美学自联的邀请,义务为柴玲作了两天的翻译。在此期间,我就向她提出了为这部影片向她采访的意愿。她当时未置可否,又岔入别的话题。而我也想到她刚结束十个多月的逃亡生活,身心都很疲惫。来日方长,我们的片子也不会很快拍完,以后再谈也不迟。
“天安门”初拍伊始,限于经费,我们先就近采访路过波士顿的人物,如封从德、项小吉、吾尔开希、戴晴等人。后听说柴玲定居工作在波士顿,成了我们的本地人,应该采访起来更方便些,于是把精力集中到散布在其它各地的人物,如去北京采访王丹、丁子霖,去台湾采访侯德健等。1994年的春天,我开始给柴玲打电话,再次表示采访的意。起先,她推说太忙,当我告诉她已接受采访的人中包括戴晴和刘晓波这些观点与她不尽相同的人时,她的言语中更是透出鄙夷和不耐烦。经过多次的电话留言和周旋后,她终于说:“我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又说:“想拍片子的人多了!”我向她解释我们影片的宗旨是严谨地处理史料,尽量包容不同声音,尽可能地让受访者最精彩地表达自己。我还告诉她,我们的片子希望尽量采用当时的影视资料,但不可能完整,当事人的回忆至关重要。由于她在运动中留下了不少资料,别人的采访中也多次提及她,赞扬和批评都有,无论她现在接不接受采访,都已是影片中的一个历史角色。我希望她能以自己的回忆与论述,使这段历史的表述更为充实和准确。然而我的诚意丝毫未能动摇她拒绝的决心。
当时我们已准备把所能收集到的柴玲在1989年的影视资料汇集在一起,以便采访前先交给她看一下,这样既可帮助她回忆,又可以针对当时的镜头提问题。我们采访王丹时就是这样做的,讨论比较充分深入。而最早采访吾尔开希时还未收集到大量的资料,于是采访与后来收集到的画面不大容易配合,有些遗憾。现在如果采访不到柴玲,影片又会有许多缺憾。虽然我实在懒得再去领教柴玲的轻蔑,但还是说服自己不要与她计较这些,还是应该尽量争取。于是请人权活动界的头号人物Robert
Bernstein给她去信,并通过与她较熟的阮铭、以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谷梅(Merle
Goldman)去游说。奇怪的是,柴玲对这些头面
人物都表现得非常乖巧,答之曰:“我再考虑考虑。”而待我再去电话时,仍是拒绝采访。我问她原因,她说:“影片不能表现真实”,并说她觉得做得好的只有Ted
Koppel的那个节目。我无可奈何,只好决定放弃。我说:“你执意不接受影片采访,我只好尊重你的决定。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帮助我核对一些事实,使影片在叙述这些事的时候不至于出错误。比如你认为好的那个Ted
Koppel节目中提到你准备离开广场,转入地下……”
柴玲马上说:“但我并没有离开。”
我说:“这我知道,那个节目里也是说你原打算离开,後来又改变了主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当时的想法----为什么想离开?又为什么决定留下了?”
柴玲说:“要回答这些,不就等于接受你的采访了吗?”
我又问:“王丹说,五月二十七日联席会一致通过了建议学生撤离的决议,你也同意了。是不是这样?”
柴玲停了许久才说,她记不清了,而且当时讨论的重点根本不是这个。她接着抱怨说外界对当时广场的气氛、学生的心情根本不了解。
我虽然这时已对正式采访柴玲不抱什么希望,但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我说:“正因为外界不了解,我才希望你能把当时的情况、你们感到的压力、你最切身的体会讲出来……”
没等我说完,柴玲冷笑一声,说道:“卡玛,你可真可爱呀!”
我意识到再说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剩下的问题是没有她的回顾,影片将如何剪辑。我有些绝望。把她省略掉是不负责任的,但要包括她这个角色,就只能用运动中间或录下的资料无法连贯,与其他接受了采访的人相比,这种处理也显得不平衡。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不得不考虑大量采用录音、录影效果都极差的柴玲“5月28日谈话”的资料。虽然这也是运动中的一幕,但它不仅表现了柴玲那一天的状况,而且也包括了她对民主、改革、当时广场形势、学生领袖之间权力之争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对运动从悼胡到5月28日一次较完整回顾。这种回顾中的回顾使得影片的时空结构变得极为复杂。另外,因为没有柴玲本人后来对5月28日那次谈话的回顾与注解,我们不得不大段大段地引用原话,以期能够尽量多保留一些柴玲当时的心情、状况,以免她的一些有争议的言辞被抽象出来理解。但这样做,又增加了柴玲“5月28日谈话”在影片中的比重,使其更加引人注目。面临许多困难的选择,我们尽量兼顾各种因素,设计影片的结构。为补救影片不得不做的节选,我们整理出柴玲89年5月28日谈话的完整记录稿,在电脑万维网上发表,使人们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资料的全貌。
1995年的春天,影片的粗剪刚刚完成,《纽约时报》报导了“天安门”的有关内容,其中引用了柴玲所说的“期待流血”等一些话,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5月28日,香港的《南华早报》上刊出了一篇采访柴玲的报导。文中,《南》报记者问柴玲为什么拒绝我的采访。柴玲称:“我告诉制片人我当时很忙,正在写书,忙过後就会接受采访。”
这些话更加深了我对柴玲的失望。我一直认为柴玲不接受采访是自己放弃了一次机会,但她有权作个人的选择,无可非议。现在却发现她不肯为自己作出的选择承担任何责任,竟然对记者撒谎。如果说当年在广场情况危急的环境下,我对柴玲的某些言行虽然不能苟同,但设身处地尚能加以理解和同情的话,那么在美国平安生活多年后的今天,她竟如此出尔反尔,难免让人想到她的这种不负责任是否有一贯性。她过去的一些表现不再是高压和年轻所能充分解释的。
尽管在影片的结构已大致定型的情况下再加入新内容需耗费可观的经费,并将推迟影片完成的时间,我仍克服了种种不情愿,给柴玲写了封信,提出既然她向《南华早报》的记者表示忙过後会接受采访,那么我们仍然愿意采访她。此信挂号寄出,同时寄了一份给阮铭,并收到了他的回信。然而寄给柴玲的挂号信却如泥牛沉海,毫无音信。待影片1996年1月在波士顿美术馆上映时,我们再次发函,邀请柴玲参加讨论会,仍未得到回应。
1996年8月9日《波士顿环球报》一篇柴玲的专题报导称“在过去的一年中,影片‘天安门’的宣传破坏了柴玲的生活。”文章指责影片以曲译柴玲的原话,来歪曲她的形象,并说“影片引起的争论导致了一些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对她进行攻击。她还收到了恐吓信,使她在美国第一次感到不安全。”我大惑不解。难道中国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不懂中文,而需要通过英文的“曲译”来理解她的原话吗?这戏是不是演得太过了一点?
中文主页 | 关于影片
| 音像图库 | 民主墙
| 六四史料 |
网站导览 | English
© Long Bow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