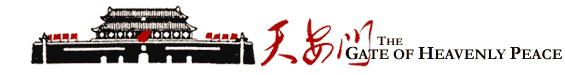 |
||||||
|
诉讼纪实(四) 4.上书人大常委会
十月十七日才拿到护照,纽约科学院邀请我在九月份参加成立175周年的庆祝活动早就过去了。中国人权将在十二月初召开理事会。我预订了十一月二十七日飞纽约的机票。我之所以还要在南京待一个多月,主要是为了完成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民上书》。 我给江泽民的信中说:如果很快出国,《申诉书》就没有必要发出去了。这话不是真的,因为领取护照受阻才这么说。《申诉书》是早晚要发出去的,而且当时我又在下最後一步棋,开始写作《公民上书》。了。《公民上书》比《申诉书》又进了一步。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是持不同政见者吗?那么,我就说说到底有些甚么不同政见。出国之前事情很多,我咬着牙日夜兼程,一定要把它写完。有人劝我,到了美国再写吧。不,同样的内容,写于南京锁金村和写于纽约曼哈顿,意义大不一样。我就是要在天子脚下说给天子听;也是保持为人的一致,不因为在国内慑于压力而不说,不因为到了国外无所顾忌而乱说。 十月二十日,我到上海的美国领事馆签证。领事馆在淮海中路的一个僻静所在。供签证出入的门外,有一条线和一个圆。沿着墙根的一条线,是等待进去签证的人们排的队,绵延三十米;据说,有时长达百余米。门口的人群形成一个圆,是为准备签证打听消息的。从门里出来的人,一看脸色就知道是签上了还是没有签上。没有签上的人,带着失望和遗憾一出门就急冲冲地走了。有的人喜形于色,特别是年轻的姑娘连蹦带跳地飞了出来,门口的人群一拥而上,团团围困,他或她就成了圆心,想走也走不了。人们问长问短,而且还互相探讨,甚么样的条件才能签上。看来那些打听消息的人,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他们对里面的美国签证官都取了外号:大胡子,黄毛。而且还研究了他们的个性:搼大胡子好说话,可别碰上黄毛挃。对于签证官的生物钟也有研究,说是星期一二休息以後刚上班,情绪不高;星期五六想着出去玩,就放松了。这一天是星期二,所以排队的人不算多。 美国领事馆前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有人出租凳子,有人代填表格,有人供应胶水(贴照片用),还有出售饮料等等。收入不错。租一张凳子一元,每天可赚五十到一百元。用一次胶水两角,而买一瓶胶水才三角,至少可用一百次。人们都这么说,要出国的人的钱最好赚。 排队等候签证的人们,因为命运相同,相逢何必曾相识,在一起就大侃艰辛的出国路。我说起领取护照加快也不快,还花了三百元。一位姑娘说:啊呀,老先生,太便宜了,你这是官价,我为这张护照花了八千元,八千! 一位小伙子不像她那样激动,沉着地说:你也算便宜的。我的护照,时间,花了一年多,钞票,花了一万多。我的见识太少,问:怎么花的?他们这才讲起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无非是请客、送礼、塞红包,用糖衣炮弹将把门的哼哈二将、拦路的四大金刚全打倒了。 另一位忧郁的姑娘说:为了出国求学,伤心透了。几次都想不干了,又一想,已经花了多少精力、财力,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吧。 那位沉着的小伙子却爆出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这样的祖国有甚么可爱?真是叫人一去不回头! 我说:祖国还是可爱的。问题是谁代表祖国?可恶的人不能代表可爱的祖国! 小伙子摇摇头,不以为然。他看到我所填的表格上的名字,忽然想起来:喔,郭老师,我在美国之音里听到你和共产党打官司厖。你现在还说祖国可爱,真不简单。 想不到在外国领事馆的墙根下进行了一场关于祖国的讨论。接着又目睹那些自以为代表祖国的人作出叫人伤心的事。 进入领事馆,在见美国签证官之前,还有三道关,都是中国人把守。第一道关是武装警察,检查手提包。录音带、录像带、照相机都不能带进去;户口本也不能带进去,不知为甚么。第二道关是干部模样的人,检查所填的表格。然後通过安全门。表格若有差错,退出门外重填。第三道关是大干部模样的人,先对你打量一番,再用官腔问人:你到美国干甚么?敁以前出过国没有?敁美国还有甚么人?这三道关的中国人,一个比一个凶,盛气凌人,呼幺喝六。坐在里面等待的时间很长,人们不免交头接耳。那位大干部模样的人就厉声斥责:不要讲话了!敁再讲话就把你们轰出去!其实他的声音比谁都大。如有洋人来签证,非但不要排队,这三道把关的中国人都笑脸相迎。申请签证的中国人看在眼里,暗暗地咒骂:洋奴!这些人名义上是领事馆的雇员,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干部。他们的真正任务是管那些到这里来要求出国的中国人。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怎能叫人相信这样的政府是代表祖国、代表人民的? 这一天负责签证的恰好是那个被中国人认为不好说话的黄毛,签上的祗有十分之二。但待人很有礼貌,即使不签还说一声:对不起!表现了对人的尊重。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在这里形成鲜明对照。轮到我的时候倒很顺利,一分钟就办好手续,他还对我说:Welcome to America! 我出门的时候也被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要我谈谈经验。我说:多年来,我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由于我上法院去起诉,才争得这个权利。我告诉你们,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谁不许你出国,你就带着这个法律去找他。我讲完後,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跟踪者。 为了准备出国,购物、制衣、签证等等,我多次到上海。每次到上海,都受到严密的监视。我常常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眼就把那些跟踪者认了出来,有好几个已是熟面孔。他们总是备有两样东西,或是对讲机或是摄像机。走在大街上,用嘴巴对着一个小包讲话,又把小包贴着耳朵听话,你看奇怪不奇怪?显然是用对讲机在进行联络。有的女青年,肩上背个小皮包,不断用手调整方向,那里面是摄像机在工作。他们的动作太蠢笨,当然也是肆无忌惮的表现。我住在弟弟家。我和妻子一出门,对面的弄堂(小巷)里就有人出来盯梢。看样子那里设了一个临时据点,全天候监视。平白无故被人监视,感受到人格上的侮辱。我的弟妇说:光起火来我要去问问伊,盯牢人家做啥?我说随他去吧,说不定还有好处,要是小流氓捅刀子,也许他会上来保护我。有一次,我们去找一个朋友,不愿给人带来麻烦,所以就要想办法摔掉尾巴。後面跟的人一高一矮。走到一处,我忽然停住,对妻子说:那边墙上贴的是道家气功,我们去看看。那两个人祗好继续往前走。到了公共汽车站,妻子说:今天没有人跟嘛。我用嘴一撅,说:在前面。一看,那两个家伙正躲在角落里用嘴对着黑包讲话。汽车来了,我们跟着大家上车。妻子刚上去,我一下子把她拉了下来,车门关上开走了。那个高个子已上车,他和我隔着车窗互相瞪眼。摔掉一个,站上还有一个,用同样的办法他不会上当了。这一回,那矮个子等我们上车以後才上来。我和妻子一个靠近前门、一个靠近後门,他在中间两头张望。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两人突然下车,他在中间挤不出来。车开动了,他和我又隔着车窗互相瞪眼。共产党教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我的资格比他们老。当年没有对讲机、摄像机之类的现代化工具,但摔掉几个跟踪者是不在话下的。 在上海比在南京对我盯得紧,而且越来越紧,後来不是从对面的弄堂里跟出人来,而是一下火车就有人在那里恭候了。我坐上出租汽车,跟踪者就钻进一辆早有准备的紫红色桑塔纳轿车尾随。他们不知道还有保护我的人在反跟踪,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53113。以後又见这个车牌的紫红色桑塔纳在我住地周围游动,就知道干甚么来了。我对这种上海景进行了思索,意味着甚么?联想起在北京时听到的秘密逮捕的传说,看来并非无稽之谈,可能是在寻找机会。我的几个神通广大的学生,又从地方上的安全部门得到一些重要信息。南京市安全局已经把我的案子交给上面。假如我失踪了,一定是在上海,因为在南京不敢下手,怕南京大学的学生闹事,而上海是我出国必经之地。所以我在上海,出门都有亲友护送,有时还进行交接班。当时听说高尔泰失踪了(到美国後才知道是出走香港),更加重了我的担心。我知道,人家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我怎样提高警惕,最终是斗不过他们的。如果历史决定中国还要有人出来再一次当李公朴、闻一多,那就是我! 我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公民上书》的。也许这就是我的绝笔,故尽我所有,铺陈纸上。但精神紧张是写不好文章的。想起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与朱光潜先生交往,他赠我一警句:持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文章。此时此刻,体会尤深。现在我就需要有一种超然出世、无所牵挂的态度,才能写好这篇入世的文章。友人送我一盒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录音带,一听顿觉思想放松。于是我到鸡鸣寺、栖霞寺去买了许多佛教音乐和念经的磁带。一听佛经,好像站在云端里观察世事,心境十分宁静。我是一面聆听佛经一面操作电脑完成《公民上书》的写作的。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我这个无神论者吸取了有神论文化的营养。 我起诉的时候就料定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正中下怀,我可以逐步升级,不断做文章。本来我想从区级人民法院开始起诉,因行政诉讼法上规定对中央机关的起诉必须是中级以上的法院,祗好减少一次。我的诉讼文书,在内容上,层层引申发挥,在篇幅上,每次翻一番。两份《起诉书》,每份四千字;《上诉书》一份就是八千字;《申诉书》应是一万六,结果突破计划,写了二万五;《公民上书》当有五万字。法院的起诉书、上诉书是有一定格式的,我全不理会,怎么痛快怎么写。有的官方法学家说我的状子不像状子,都是论文。这就说对了。如果我写成论文,非但无处发表,说不定真成了反革命煽动;写成状子,则可以合法流传。不少人还向我请教,状子怎么写,我成了义务法律顾问。我本来想到九点不同政见,《公民上书》写了五点,已达五万字。事情很多,时间很紧,祗好就此打住。这一时期,我日子过得更苦。《公民上书》的最後虽写着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一日于南京紫金山下锁金村,实际上到我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才改完、定稿。我委托别人打印以後,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寄送给万里委员长和诸位副委员长,同时寄送给江泽民和邓小平。 起初,我想悄悄地行动,所以出国的日期、航班、路线都保密。香港的《南华早报》对我进行采访,我故意施放烟幕,说是圣诞节前离开上海,经底特律到肯塔基看望儿子,然後去纽约。後来发现,我的行踪别人了如指掌,无法保密。我的学生说,干脆都公开,大张旗鼓地进行。我采纳了这个建议,改变方针。香港《联合报》来电话询问近况,我如实地说明处境和行程,最後强调一句:如果我十一月二十七日没有到达纽约,请你们作追踪报道。我一方面诉诸海外舆论,一方面依靠群众保护,同时又给当时领导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写了一封信,提出我的安全问题。最後有一个附注:此信复印件已托人带去美国和香港。如果我遇有不测,则将公开发表。到美国以後,我在发表于《世界日报》十二月六日的一篇文章中声明:现在我已经到达纽约,虽然不太顺利,人总算还是完整的。这封信就不发表了。我是守信义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离开南京。我的友人和学生几十人在大楼前、火车站热烈欢送,还有人陪同我到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去虹桥机场,祗有两位亲戚送行。我估计到会有麻烦,航班是九点五十分,我七点一刻就到了。果然,以前认出来的跟踪者的熟面孔都来了,他们周围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前前後後,里里外外,跟着我。我和旅客们一起排队进去的时候,被单独叫出来,打开行李翻箱检查。一位看起来比较负责的人问我:带文件了吗? 没有。 有计算机软盘吗? 有。我拿出四张软盘。 他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子里,隔着玻璃门在外面望着我的亲戚非常着急。 他问:甚么内容? 主要是我打官司的法律文书,还有已经发表过的文章。 他说:我们要检查一下。他拿出去过了一回又来,说:电脑有毛病,留在这里吧。 我说:不行,我要带走。我不相信你们这个大楼里面祗有一台电脑。 他无话可说。出去了一下又来,说:还是打不开。这样吧,我们写个收据,叫你家里的人来取。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出具证明,可以寄给你。我想,主要是那几十万字一时看不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的。我祗好妥协。(後来我弟弟去取时,说有反动内容,要没收。我写信给海关,请他们说明反动内容具体所指,并提供没收的法律根据。他们又改为退内处理,通知我弟弟去领。)其实,同样的软盘有三套,一套请北京的朋友带出国,还有一套交给了比我晚几天出国的南京朋友。我带上一套让他们没收,是为了掩护这位朋友,放松对她的警惕。当他们将我的软盘退内处理时,另外两套早已带到美国,《公民上书》也发表了。中国的官方人士不懂得甚么是现代社会,也不知道那一套愚蠢的、野蛮的办法根本不灵了。 他们又从我的包里查出二十几盘录音带,一看,大部分是佛教音乐和念经,问:你信佛吗? 不信。 这就更要检查了。别人去检查录音带,那位负责人就同我谈谈。 你在南京大学教甚么? 我是教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许我讲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美国却欢迎我去讲马克思主义。你看说明了甚么?我的反问使他为难了,他笑笑。 他问我的经历。说:老革命嘛! 我说:老革命差一点成反革命了。 越说越客气,他自我介绍,叫陈祥伦,是海关的副关长。最後,录音带送还给我时,他说:我们是执行公务,请原谅! 检查完了,两个箱子被翻得一塌糊涂。我不客气地说:请你们帮我整理好。陈副关长命令两个穿制服的人把我的箱子弄好。我又说:请你们帮我托运。他们就去托运。 过安全门的时候,对别人都用仪器,对我却用手摸。上上下下,搜了三遍,把我口袋里的手帕、纸片等等都抖落了出来。仪器祗对金属有反应,他们要在我身上搜的显然不是炸弹之类的东西;但精神上的炸弹又怎能搜得出来。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我是最後进入机舱的。门口早有人在那里等着,这一回干脆把录像机拿在手里了。我向他们招手:感谢你们来欢送!即将进入机门,我回头一看,录像机还在我背後工作。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安全部门也落入苏联克格勃的命运,把他们的全程录像拿出来,就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机场的最後一幕,我想和以前不同。以前是我怕他们采取行动,这次是他们怕我采取行动:发表演说?接见记者?散发传单?几十个人拿着家伙对付一个文弱书生,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坐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机起飞、腾空,我一下子感到自由了,此时才觉察精神上的紧张状态已维持了几十年。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一点半,我到达纽约。从被剥夺出国的权利到争得出国的权利,是以我的胜利告终。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还是一条艰险的道路。但是,虽然开动了专政机器,终究不敢轻易下手。在现代条件下,合法斗争毕竟比其他的斗争方式更有成效。 *季遵迪也是中国人权理事。我到美国後,常与他一起参加中国人权理事会和其他人权活动。他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行政诉讼法,还邀我合作共同讲课。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他突然昏倒在纽约街头,不幸身亡,年仅三十九岁。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扼腕长叹!每念及他和我的交往,对这位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友人常怀由衷的敬意。**我当时不知道,《百姓》半月刊(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这一期,陆铿新闻信《郭罗基获准赴美,临行前特务盯梢》已经披露。後来《探索》(纽约)一九九三年一月号在《郭罗基出国记》一文中又发表了。我本人身边已没有这封信,也好,录此存照。《探索》的文章中说:郭罗基致乔石书,不仅有政治意义,且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政治意义虽失,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犹存。信件已在美国和香港流传,殆非郭罗基和乔石私人所有。公诸报端,亦不悖情理。原信如下:乔石同志:我早就听说,国家安全部已将我列入秘密逮捕的名单。不知是否属实?如果确有其事,我想学毛泽东的腔调讲一句:第一反对,第二不怕。今年五月,美国纽约科学院选举我为院士,并向我发出访问院本部的邀请。随後,哥伦比亚大学又向我发出讲学的邀请。我申请出国,虽然遇到种种麻烦,花了整整四个月,总算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但在我出国之前,又对我进行严密监视。一方面批准出国,一方面严密监视,这种不协调的现象祗能有一种解释:中国政府是为了装出宽容的姿态,并使我产生麻痹,以便寻找机会动手,干得不露马脚。 昨天,我到上海办事。一下火车,就有三个便衣在那里恭候。今天我出门,又有人紧跟不舍。他们手持对讲机,不断请示汇报,不知要干甚么?我一眼就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把他们认了出来。共产党教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资格太浅。他们的动作太蠢笨,当然也是肆无忌惮的表现。无论如何,要好好提高业务水平。我一向主张以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争取人权,实现自由和民主;我还反对党和政府的非法、违法行为。按照现行法律,不可能对我作出处置,所以就会有人想到用卑鄙手段进行暗害。既然是暗害,就不能让人家知道;既然人家已经知道,还有甚么意思?一意孤行,将在政治上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景仰谭嗣同、邹容、李大钊、李公朴、闻一多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果历史决定我要步他们的後尘,我义无反顾。解放前,我就被国民党无锡城防指挥部列入黑名单。由于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过长江,我才得以逃脱追捕。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由共产党来完成,那就说明我命中注定要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作出牺牲。而十六岁没有作出牺牲,到六十岁再补上,已经多活了四十四年,何足惜哉!(陆铿新闻信中说:我读到这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其悲惨!而铮铮铁骨之士所反映出的民不畏死的精神又何其壮烈!)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管束您的部下,不要胡来。我的行动计划,他们已得知,干脆就公开。我将在本月二十四日离开南京去上海,乘二十七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赴纽约。我也已通知美国的朋友,如果在这期间我突然失踪或发生意外(例如车祸、中毒等等),他们会立即作出反应。 但愿我能平安到达纽约。 祝我的祖国前途光明! 郭罗基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写于上海 又及: 此信复印件已托人带去美国和香港。如果我遇有不测,则将公开发表。 十一月二十日寄于南京 |
中文主页
| 关于影片 | 音像图库
| 民主墙 | 六四史料
| 网站导览 | English
©
Long Bow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