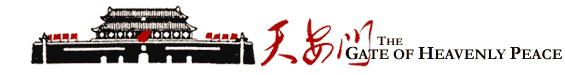 |
||||||
|
诉讼纪实(三.三) 3.申诉
我在北京会见了不少老朋友,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多次找法学家朋友请教、座谈,大有得益。我想起了高尔泰的感慨,他说在四川呆久了就会有盆地意识,他每年要到北京去充电一次。北京是出思想的地方。 我在北京又参与了另一起诉讼活动。 《历史的潮流》编委会是一批年轻人,负责人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袁红冰。中国的官方人士说:自由化分子已经是老中青三结合了。一点不错。我离开北京以後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自由化分子,更有活力,更难对付。《历史的潮流》编委会对于後来出现的结果早已估计到,事先采取了措施。出书前,弄到一张薄一波的题词:改革开放,强国富民。出版社这一关就容易通过了。出事以後,薄一波说话了:稿子我没有看,秘书说写得不错厖书印好後,先将外地的发走。准备在北京出售的,也提出来藏在一个地下室,给出版社留了四百八十本,让它去查封。《历史的潮流》在北京一亮相,果然遭查封。其实损失不大;相反,官方禁书的影响比任何广告所起的作用都大,人们倒想看个究竟。《历史的潮流》不能进新华书店,就流动出售。拿出两千本到中共中央党校,一个中午就卖光。第二天到王府井,第三天到前门,厖到处打游击。後来还出现黑市,本来定价4.45元,有人卖10元、20元,最高达30元。书贩子见有利可图,纷纷盗版翻印。结果这本书发行了好几十万册,至少比正常的发行多十倍,还要对左派表示感谢。 《历史的潮流》编委会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以座谈邓小平的讲话为名,进一步反击左派的挑衅。北京有过这种怪现象:自由化分子集会,或是临时会场另有别用,或是停电,致使会议开不成;要不,会议开了,来了一些不相干的人捣乱,叫你开不好。这次座谈会,公开通知的地点是中共中央党校,真正的地点祗有几个人知道。当天早上,会议的组织者把应该到会的人接到了奥林匹克饭店,而另一些人就跑到中共中央党校去了。会议的参加者九十多人,座谈了五个小时,发言很热烈,香港和国外广泛地作了报道。 无论从哪方面说,《历史的潮流》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反对者担了恶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还违了法,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经多次商量,决意进行法律诉讼。由《历史的潮流》编委会负责人袁红冰,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和新闻出版署。袁红冰任诉讼法教研室副主任,打官司是看家本领。虽然都是告共产党党委,和我的起诉角度有所不同:人民大学党委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历史的潮流》被封存的直接原因是人民大学党委违法下达的行政性命令,所以它实际上起到了相当于行政机关的作用。为了使合法权利得到救济,故将人民大学党委列为被告之一。袁红冰曾向新闻出版署请求保护公民的合法著作权,没有结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所以,新闻出版署并列为被告。七日期满,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袁红冰补充起诉的法律根据,显然是拖延时间。补充多少法律根据都没有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下了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理由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所说的十分相似: 一,人民大学党委不是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二,人民大学党委对人民大学出版社进行监督管理是学校内部行政行为; 三,《历史的潮流》的封存不属于新闻出版署管辖。 袁红冰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甚么理由都不说了,祗有一句话:对袁红冰的起诉不予受理是正确的,驳回上诉,作出终审裁定。北京的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比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差劲多了。 我在北京期间,正值六四三周年前後。别看大家都在捞钱,北京人没有忘记六四。有一次,我坐出租汽车经木樨地,司机指给我看大楼墙上的弹痕,就是这座楼,一个六岁的女孩,在阳台上被打死後掉下来厖。这也是反革命暴徒?但是人民还在克制。北京大学的学生宣告: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提出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表示支持,所以今年六四暂时不采取行动。尽管如此,紧张空气并未稍减。从五四前开始,一个多月,北京大学处于非常时期。外有警车嘶鸣,内有便衣巡逻。严格把守大门,外人不得入内。我是北京大学的校友,也遭拒之门外。 六四前夕,北京的高等学校普遍传达了一个敌情通报,其中居然有这样一条:郭罗基到北京厖。一个文弱书生到了北京,如临大敌,实在是神经太紧张了。我本来要去参加奥林匹克饭店的座谈会,当天早上有人打电话叫我不要去,说是甚么原因以後再告诉你。第二天,他来,说是得到可靠消息,我已被列入秘密逮捕的名单。我说:不可能吧,秘密逮捕不是早就被毛泽东否定了吗?斯大林时代有秘密逮捕法,多少人突然失踪,连元老伏罗希洛夫都担心,早上出门不知晚上能否回家?五十年代,罗瑞卿当公安部长时也想学习苏联。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秘密肃反是不赞成的,他的拿手好戏是搞群众运动,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他有本事公开把人打倒,再踏上一祗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就不必来秘密的了。 来客说:现在谁有毛泽东的本事?说不定就把老式武器搬出来了。 我问:怎么个秘密逮捕? 据说,第一,要寻找机会,干得不露痕迹。或是失踪,或是制造车祸、食物中毒等等,连家人都不会怀疑是政治原因,而是偶然事故或自然死亡。第二,等待形势的发展。如果邓小平一死,政局难以控制,那么有影响的自由化分子就要马上除掉。要干,是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负责,地方上的安全机关都信不过。我说:为甚么不能参加会议?他说:主要是怕把盯着你的人引到开会的地方,对会议不利。我问消息的来源,他说是在国家安全部担任司长的一位朋友告诉他的。他们这些人担心将来会落入苏联克格勃的命运,想留一条後路。所以故意向我放风,为的是必要时可以让我为他作证明。我还是将信将疑:既然要寻找机会,不给他机会就是了。後来得知,六四前後有三十多人被捕,可见专政机器还在加速运转。从前抓了人就登报,以为能起威慑作用,结果招致国外抗议,国内的人民也受到鼓舞,知道六四火种不灭。现在抓人悄悄地进行了。这倒是一种转变。 如何在中国大陆开展人权运动,我和朋友们也进行了商量。我们这一批人有几十年患难与共的经历,相知颇深。有一次相聚,某人这样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假如一个警察进来,说:你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砍脑袋,其他人走开。我相信都会站出来,没有人走开。我提名王若水、于浩成为中国人权理事,于浩成不久前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爽朗地说:义不容辞!不久,纽约中国人权总部通过。这样中国人权在大陆就有了三名理事。我们几个人年龄大一些,活动能力较差。我们背後还有一大批年轻人,他们是实干家。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目的已经达到,头脑完成充电,又回到南京,赶写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 《申诉书》不再纠缠已经提出的问题,而是从我的案子出发,向深广两方面发展。在北京时就拟定了三个题目: 一,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服务必须严肃执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哪一家法院可以受理侵犯人权的案件? 三,思想不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党和政府却常常用违法犯罪行为来对待思想。 第一个题目是反左,法院也必须反左,否则不可能严肃执法。 第二个题目是进一步用我的经历说明至少有九种关于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或竟遭剥夺,而我的起诉仅仅涉及劳动权和出境权,还有七种关于基本人权的受害状况尚未诉诸法律。请问最高人民法院,到哪里去告诉? 第三个题目是从我所受的政治迫害出发,推而广之,控诉惩罚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的一系列专横行为。从反胡风、反右派一直说到反自由化,特别要说一说我们这些自由化分子的共同遭遇。但一九八七年那一场反自由化,我不在北京,虽然听了不少,下笔时就觉得材料不太确切,祗好简单交待一下,非常遗憾。 我的《起诉书》、《上诉书》在国外发表後,引起不少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专家们的注意,《纽约时报》和《人与人权》刊出了评论文章。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季遵迪(TimothyGelatt)*,还为我写了一份详尽的意见书。我惊叹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研究之精细,一一采纳,补充了申诉的法律根据。 写作《申诉书》时,正值南京盛夏。南京是中国著名的火炉,白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度。家中无空调,电脑不能起动。我经常在半夜工作,还要用许多冰块在电脑周围制造凉爽的小气候。白天闷热,又有种种干扰,无法睡觉,苦不堪言。我付出了极大的毅力和精力,才把《申诉书》写完。但并没有立即送出去,因为又出现了新情况。 六月,我收到纽约科学院选举我为院士的通知和院士证书,还邀请我参加将于九月份进行的纪念该院成立175周年的庆祝活动。我又一次写了办理出国手续的申请,连同有关材料,于七月二日送交南京大学校长。正巧,当天又收到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J.Nathan)教授来信,邀请我九月以後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当访问学者。第二天再给校长送去黎安友教授的邀请信。这样,我在参加了纽约科学院的庆祝活动後,就可以在美国逗留较长的时间。 这一次对我出国的审批,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说:我们不管了。而且校长、副校长们也立即同意,将报告转到北京国家教委。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下办事效率可高啦,先发电传,再寄原件。法院对我的起诉虽然不予受理,共产党党委的出国审批权似乎动摇了。共产党的脾气就是这样:别人批评,死不认错;这一次气壮如牛,下一次偷偷改正。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有一个整改阶段,把右派分子打下去以後,再按右派分子所提的某些意见进行整改。大跃进失败了,先把以彭德怀为首的批评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整肃,然後就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我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南京大学的负责人显得很轻松:我们早就同意了,问题在国家教委。八月中,国家教委在南京大学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我的一位朋友去找了他们的张处长。张处长和我并不相识,对我的事情很热心。她给北京打了几个长途电话,总算弄清楚了。南京大学的报告送到国际交流司,说是同意南大的意见,又送到直属司(管重点大学的事);直属司同意国际交流司的意见,又送到委领导。在委领导那里已有一个多月,不知是否又送到别的甚么领导那里去了。我的朋友问张处长:怎么那样麻烦?答曰:因为是郭罗基嘛,一路都说同意,就是没有人最後作主。 又过了一个月,九月十二日,我得到通知,可以办出国手续,但先要办离休手续。不知是谁最後作的主。先离休,後出国,其中有何奥妙?经多方打听得知,受到国外的邀请,又有经济支持,经官方批准,叫做自费公派。我本应属于自费公派。离休以後,叫做因私出国。当时,我还是没有弄清两者区别的意义,到美国以後才恍然大悟。如果是自费公派,将来没有理由拒绝我回国;而因私出国,就可拒我于国门之外。原来早有伏笔。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已被共产党革出教门,老干部的身分是取消不了的。和退休不同,老干部离休以後仍领取百分之百的工资。但我的工资被剥夺得所剩无几,为了表示抗议,早就拒绝领取。我声明:离休,按制度办事,我可以接受。但离休以前遗留的问题仍需要解决。不要以为法院不予受理就完了,官司还要打下去。当时正在放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我调侃了一句:杨乃武的姐姐告了一百多次,我才告了几次? 我说:那个百分之百的工资,我还是不去领。甚么时候为我平反冤案,我才去领。 同我谈话的人说:郭老师,有问题以後再说,工资还是去领,否则财务处不好办厖 我就是要你们不好办。其实,职称和工资我都不在乎,我是为了给你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整人是难以收场的。 多少年来,我像大熊猫和珍贵文物一样,是被禁止出口的。现在居然被批准出国,消息传得很快。办理出国手续,又开始了另一个曲折而有趣的故事。 在人事处、老干部处、保卫处、校长办公室之间转了好几天,九月十六日办完了南京大学的手续,花10元拿了一张介绍信,到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领取护照。交验材料时,要求将英文的文件译成中文,公安人员给我指定一个公司的出国服务部,交费40元。我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我自己翻译一下。 你自己翻译得准确不准确?翻译得准确,盖章公证,也是40元。 反正是要你出钱。自己翻译,说你不准确,又要惹麻烦。我交了40元,还得两天後来取。十八日取到翻译稿。一看,总共一张纸,祗有五六行。英文的文件有五个,祗译了IAP?6表,而且也祗译了几项。字迹潦草,标点不全,文句不通,大概花了十分钟。重要的是盖了一个章。一个公司的出国服务部的图章为甚么能起公证作用、具有法律效力?就因为它是公安局指定的!中国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外文文件必须译成中文才能生效,而外国的大使馆、领事馆签证时也并没有要求中文文件必须翻译成外文。时下中国人认为出国就是发洋财,想尽办法勒索,叫做雁过拔毛。 我到出入境管理处交上五个英文文件和一纸译稿。公安人员给我一张表,上写材料齐全,又叫我到那个出国服务部去交钱。 问:你是不是要加快?不加快25元,加快150元。 不加快是怎么回事?加快又是怎么回事? 不加快一个月,加快是一个星期到十天。 我当然要加快,交了150元。中国政府声称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本应讲究效率,现在却要人民出钱来买他们的效率。实际上他们能快也不快,而办理出国手续的人的心理总是尽量要快,这又是逼得人多交钱的一个花招。加快和不加快,做法上有甚么区别?出入境管理处收到申请後,要进行政审(政治审查)。如果不加快,将政审表寄到申请者所在单位的保卫部门,保卫部门填写後再寄回。所谓加快,不过是将政审表派人送去又取回,省了邮寄的时间。出入境管理处是政府部门,出国服务部是民间机构,他们到底是甚么关系?公民向政府申请护照,为甚么要向一个民间机构交钱?150元的定价又是根据甚么成本核算? 我拿了出国服务部的收据,又到出入境管理处,这才给我三张正式申请护照的表,还要交105元。 公安人员对我说:你拿回去填,明天再来。 为甚么? 我们五点下班,你来得及填吗? 我一看时间是四点半。我是三点到达的,在出入境管理处和出国服务部之间来回折腾,花了一个半小时。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给人民找麻烦,我明天再来路上又得花两个小时。一般的机关是六点下班,他们提前了一个小时,而且四点半就准备收摊了。 我说:我可以在你们下班前填好。那三大张表确实很复杂。我来的时候就看见几位女士坐在那里填,大概生怕填错,一边填一边想,我走的时候还没有填好。我精神高度集中,用二十分钟就填好了。 那些准备下班的懒洋洋的公安人员,见我居然填好了,反倒打起精神来了。左看右看,挑出毛病来了:这一栏你没有写清楚。 那一栏是出国联系经过。我说:我已经写了,是对方邀请。 你要写上甚么时候开始的?怎么联系的?通过甚么渠道、甚么人?履行过甚么手续? 没有,甚么都没有。我没有去联系,是对方主动邀请。 你没有联系人家就邀请了? 是的。 哪有这么回事!人家为甚么要邀请你?这些人是一派殖民地心理,好像非要乞求洋人才能得到邀请。 因为他们选我当纽约科学院院士,当然要邀请我去访问。 那么他们为甚么选你当院士?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笑了起来,随即脸色一沉: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们,我怎么能回答!他大概也觉察问题提得不对头,自己找个台阶下:那是因为你有学术地位,就把这一点写上。 已经过五点,他们急于下班了,最後对我说:没事了,在家等着吧。 在中国办事是能不在家里坐等的,需要顺藤摸瓜,一个一个环节往下摸。下一个环节是到南京大学保卫处问,甚么时候收到政审表,希望尽快完成政审。虽说是加快,过了三天才送到政审表,比邮寄还慢。在保卫处遇到好人了。他们催促各级领导签署意见,然後,不等出国服务部来取,就直接派人送到公安局。保卫处长对我说:我们一分钟也没有耽误。 十天过去了,护照毫无消息。我打电话问出国服务部,回答道:出入境管理处说的,你有问题,快不了。我亲自去出入境管理处问,究竟有甚么问题?公安人员反问我:谁说的?我们没有说,谁说的你去问谁。他倒变被动为主动了。 搮你的护照嘛,正在进行中。一个月给你答复是正常的。 我说:我在出国服务部交了加快的费用,怎么快不了? 出国服务部怎么能决定我们快不快? 我说:那是你们叫我到那里去交钱的。 你找他们退钱。 我和公安人员对话的时候,旁边一位女士,也是办理申请护照手续的,和我素不相识,一个劲地拉我的衣服,暗示我不要同他们顶。这是善良的中国人。中国人和政府打交道好像低声下气、打躬作揖才是,像我这样似乎不合常规。听公安人员的口气,确实有问题。一个月之後祗是给个答复,怎样答复?不得而知。我的《申诉书》写好後按兵不动,现在要当作炮弹发出去了。我通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也寄给江泽民、邓小平。十月一日,还有一封给江泽民的信: 按惯例送上我的《申诉书》一份。 《申诉书》在七月初就已经用电脑写好。当时我收到纽约科学院选举我为院士的通知,并邀请我访问院本部;接着又收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的邀请。我又一次申请出国,承蒙南京大学和国家教委转辗批准。如果很快出国,《申诉书》就没有必要发出去了。近日,我在南京市公安局领取护照受阻,于是我想《申诉书》还是要发出去。所以前两天才送交法院。 这封信,我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念给纽约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请他记录下来,在美国和香港发表。果然有效。消息传出,是这么回事。在我之前,国画大师刘海粟领到护照後,出国不归,声言:搼六四不平反不回国。李鹏派袁木到南京来查问。这是毫无道理的。南京市公安局过于谨慎了,认为郭罗基也是敏感人物,于是层层向上请示。外面造出舆论,上级又发话了:你们为甚么不早给他护照?下级不好当。刘海粟的护照,给了,吃批评;郭罗基的护照,不给,又吃批评。十月十五日,公安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很客气:你的护照可以取了。但是现在护照要换一种式样,做起来很麻烦,请你等几天。十月十七日,我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去公安局,说:今天是法定时间的最後一天厖他们说:好了,好了!随即把我的护照拿了出来。我又说了一句:你们真能充分利用时间。公安局的人也并非都是恶狠狠的,一位女干部名余海霞,和颜悦色地说:对不起,我们耽误了时间。祝你签证顺利,出国一路平安! 到了法定时间的最後一天才拿到护照,算甚么加快?按理说应退我加快的费用。出国服务部却说:有意见可以提,钱不能退。提意见有甚么用?没有用的意见何必再提?在走廊里、电梯里遇到从出国服务部办事出来的人,无不愤愤然:这个出国服务部恶劣透了,死要钱!敁挂着服务的招牌,究竟为谁服务?问题是它还可以继续恶劣下去。拿到护照的人,又忙于签证等等,无暇计较;没有拿到护照的人,下次还要上门,不敢得罪。 |
中文主页
| 关于影片 | 音像图库
| 民主墙 | 六四史料
| 网站导览 | English
©
Long Bow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