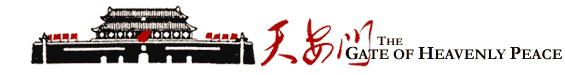 |
||||||
|
诉讼纪实(三.二) 2.上诉我提前两天,于三月十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递送了《上诉书》,同时也寄给了江泽民和邓小平。 上诉是不能不受理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我交了八十元诉讼费。 《上诉书》比《起诉书》传得更快、更广。我直接散发的就有一百多份。我的学生朱利全从别的地方复印了三十份,刚进校门,就被一抢而空。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一家饭店遇到一桌年轻人在朗读我的《上诉书》,大概已有醉意,还不时大声叫好。 我给江泽民的信中说:“不知哪些义务宣传员把我的两份《起诉书》送到BBC、VOA和一些外国报纸。为了照顾新闻的连续性,这一次是我自己把《上诉书》的副本寄给了外国通讯社驻北京记者,同时也寄给了新华社。”我是寄给路透社的史进德的,请他复印以後分送。结果,路透社发了独家消息,其他记者打电话来要《上诉书》全文。我问史进德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不能给他们。”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比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更随和,祗是打了一个电话,请我在四月十日到行政审判庭去“谈谈心”。也是一位审判长、两位审判员、一位书记员,我坐定了还给我端茶。 审判长:“这个案子我们是很重视的。我们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案子,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次。”他要我谈谈为甚么起诉、为甚么上诉。 我谈完後,一位审判员手里拿着我的《上诉书》,抖了一抖,自言自语地说:“确实是一篇好文章!” 审判长:“你要不要请律师辩护?” “不需要,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审判员:“恐怕南京的律师还不敢为他辩护。” 另一位审判员:“律师辩护也不一定比他本人说得清楚。” 我说:“我能不能提一条意见?” “可以呀!” “我的《起诉书》是两份。对国家教委的起诉是行政诉讼案件,理应由你们行政审判庭来审理。但对南京大学党委的起诉本来就不是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行政诉讼法,由你们行政审判庭来审理是不合适的。” “你看由谁来审理?” “我提出的是一起共产党违法案。现在没有审理共产党违法的法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网的大漏洞。我认为,可以暂时使用民事诉讼法。共产党的党委作为团体完全具备被告的资格。因此,这一案件应由民事审判庭来审理。” 审判员:“作为民事诉讼也不合适……” 审判长:“现有的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没有相应的法庭。” 我说:“我来提一条建议,经申报批准,可以成立特别法庭。” 审判长:“你出了一个主意。可是解放以後祗成立了两次特别法庭,一次是审判‘四人帮’,一次是……” 我不等他说完就接着说:“既然有了两次就可以有第三次。” “你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去提。” 确实是谈心,气氛很融洽,有些话书记员都没法记。但最後他们说,这都是个人的意见,不算数的,要听审判委员会的。 一位审判员问:“假如审判委员会驳回你的上诉,怎么办?” “我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郭教授,你对司法程序很熟悉嘛!” “逼得我非学不可呀。” 在这之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把校长和党委负责人请去谈话,详情不得而知。但他们回来以後很不满意,扬言:法院成问题,还说郭罗基很讲道理、水平很高。法院是甚么立场?究竟是站在郭罗基一边,还是站在党一边?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偏见。在他们看来,法院应是共产党的工具。 两级法院对我很客气,特别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明显地同情于我。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都在期待:是不是会有戏剧性的结果? 法律规定,对上诉的审理不得超过两个月。五月八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又打电话来请我去谈谈。这一次气氛与上次大不相同。 审判长:“审判委员会决定驳回你的上诉……”他请一位审判员解释《裁定书》。 审判员没精打采地解释了一下,将《裁定书》交给我。我仔细地看了一遍。内容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差不多。看来是由两级法院後面的人定调的。因此,我也不必同我面前的法官辩论了。我祗是说:“《裁定书》没有针对我的上诉理由回答问题。我还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最後,审判长提了一些希望。他说:“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法律的途径走不通,还可以走别的途径。”态度很诚恳。他当然知道为甚么法律的途径走不通,在司法不独立的条件下当法官,别有一番苦衷。我也知道法律的途径走不通,知其不可而为之,自有一番深意。 上诉虽被驳回,但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BBC和VOA又一次播出关于我上诉的新闻。《中国之春》分别发表了《起诉书》和《上诉书》,还有胡平的一篇文章。他以深情的笔调写道: “去国五年,我时常想到郭先生。我十分忧虑他险恶的处境,也十分挂念他多病的身体。看到海外一般关心大陆问题的人们,不论是华人还是洋人,有许多对郭先生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我焦虑,甚至愤慨。愤慨于中共的‘封杀’,愤慨于媒体的善忘,也愤慨于世人的不求甚解。我直欲大声疾呼,又恐对郭先生造成不利。当我读到郭先生的《起诉书》时,感到再也不能沉默。”胡平以警句式的语言结束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 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共同发表声明给予有力的支持: “我们十分佩服郭罗基在《起诉书》和《上诉书》中对公民权利和法制精神的阐述。我们认为,郭罗基提出起诉和上诉的行为,已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我们也知道在今日中国的大陆,郭罗基发表那些看法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我们也呼吁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来关心郭罗基的命运,以促进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改善。” 五月,中国人权(纽约)执行主任萧强来电话,通知我中国人权已增选我为理事。他意味深长地说:“郭先生,你根据你的处境来考虑,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我们能理解。” 我说:“早就考虑过了,完全接受,我愿意在国内同你们合作,推进中国的人权事业。” 外国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驻北京的记者纷纷来电话核实,问中国人权选我为理事是否确有其事?问我本人是否同意担任中国人权的理事?我一一作了肯定的答复。然後他们以“中国人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位理事”作了报道。 萧强担心我的“处境”,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从北京到南京,我已经习惯于一种特殊的生活。多少人像害怕传染病似的躲着我;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则千方百计地保护我。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内部信息有时也会通过几道接力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已经感觉到有无形的锁链束缚着我。我家里的电话“有鬼”,不用它也会出声,用它则有回声。我出门常有人跟着。我托一位女士带封信到美国,约好一个地点交给她。她发现“有人盯着我们”,吓得她不敢带了。有一次,我和“六四”以後被“收容审查”的段小光在一起,发觉後面有异样的目光。段小光回头一看:“这家伙,就是到深圳抓我的人。” 中国政府往往用“海外敌对势力”来指称海外的人权运动、民主运动及其组织。我当上了中国人权的理事他们究竟如何处置?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中国政府的态度。後来得知,外国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中国政府对郭罗基担任中国人权的理事是甚么态度?”外交部发言人说:“无可奉告。”很好,我要开始活动了,上北京去!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九日是我六十岁的生日。北京的朋友们早就邀我去北京,为我祝寿;也是纪念被逐出京城十周年,“而今刘郎又重来”。我要去北京,为的是两件事。一件,我的诉讼还有两步棋:下一步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肯定不会有甚么结果,最後一步我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这两步棋主要是在政治上、理论上借题发挥,扩大战果。我要和北京的朋友们好好商量。另一件,就是研究一下中国人权怎样在大陆开展活动,还要提名增加几位大陆的理事。 我打电话请人买火车票、飞机票,一个星期毫无头绪。有人本来很有把握,到时候还是吹了。这就怪了。传来一个信息,说是上面有话:胡绩伟、张显扬在北京闹得很厉害,不要让郭罗基去北京。原来如此! 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北京坚持改革开放的理论家们编了一本反“左”的论文集《历史的潮流》,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久,“左”派势力紧张策划,称之为“政治坏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出面,下令封存、停止发行。此事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胡绩伟、张显扬不过是论文的作者之二,因为他们名气大,罪责都算在他们的账上。 北京,我是非去不可。已经到了五月十七日,还是买不到票。我打电话到东华饭店,约定时间去找X,吸取了教训,电话里甚么事也不说。谁知这个东华饭店实际上是江苏省公安厅的招待所,自投罗网了。我一到,X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小声地说:“郭老师,甚么事?你还没来,公安厅八处的监听车就来了。”他还指给我看楼下停着的一辆带天线的米黄色小轿车。我说明来意,他为我四处联络。最後高兴地说:“民航有三张明天的退票,快去,四点半以前赶到。”当时已是四点。我的学生朱利全陪我坐出租车到民航大楼时,那辆米黄色小轿车已先到了。X转托的是Y,找到了Y,他认为没有问题。Y去了售票窗口回来,有问题了,说是“上面来了一个电话,有首长要去北京开会,需要五张票,三张还不够呢。”不一回,有人持江苏省公安厅的介绍信,把三张机票取走了。我让朱利全赶紧打电话找人买明天的火车票,他说有希望。我一看,那辆米黄色的小轿车开走了,大概又去部署下一步了。我对朱利全说:“不买火车票了,就在这里解决问题。你再去找Y,请他一定想办法帮忙。”朱利全买了一条好烟,孝敬Y。Y到售票窗口嘀咕了半天,想出办法来了。他给我弄来一张票,笑嘻嘻地说:“这是一张‘空头支票’。你明天早点去机场,先把登机卡拿到手。谁最後一个去就算倒楣,等下一个航班吧。”我皱了一下眉头,没有办法,祗好接了这张坑害别人的机票。一条烟起了作用。我问朱利全,多少钱?“八十元。你看,腐败也有好处,否则办不成事。” 第二天,起飞的时间是下午一点,我又怕发生甚么“交通事故”,上午九点就出发了。我总算没有使朋友们扫兴,赶在六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到达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