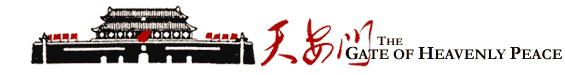 |
||||||
|
诉讼纪实(三.一) 我的两份《起诉书》早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就已用电脑写好,预定发出的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为甚么?因为这是学期的最後一天。他们剥夺我的工作权利的一个说法叫做“缓聘”。如果起诉早了,他们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马上就聘;到了学期的最後一天,这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有充分的时间将写好的《起诉书》多方征求意见。在南京,我的朋友和家人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做法,都说“太危险”,“弄不好扣一个‘反革命煽动’的帽子,把你抓起来”。有几位很动感情地劝我、求我,说是一定不能发出去。“你不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家里的人呀!”我非常非常地为难。这种经历从前已经有过。“文化大革命”後期“批邓”的时候,我拒不表态,成了“大辩论”的对象。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辩论,还不行吗?”“革命群众”大吼大叫:“就是不行,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没有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完全是亲身体验。白天,“革命群众”找我开会“大辩论”;晚上,亲朋好友登门轮番劝说:“你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更难熬;善意的劝说比恶意的批判压力更大。现在,我又一次违拗亲朋好友的苦口婆心,一意孤行。但後来我上了法院,他们就转为积极支持了。这是善意和恶意的区别。 我也认真地考虑了不同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准备在将《起诉书》送法院之前先带到北京、带到香港、带到美国,以防在无声无息中被扼杀。 恰好闽琦来南京看我。他和陈子明、王军涛一起,原在民办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六四”以後,研究所被解散、几百万元资产被没收。他逃亡到内蒙,以采药为生。躲了两年多,回到北京,不再抓他了。没有工作、没有户口,倒也自在,所以有时间到外地跑跑。他看了我的《起诉书》,大为赞赏。我就托他带到北京,大量复印,广为散发。他还说,他也要进行合法斗争,告派出所无理吊销户口。 我又通过多种途径、几经曲折把《起诉书》带到香港和美国。 1.起诉一月二十五日,我将两份《起诉书》用挂号寄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将副本寄给江泽民和邓小平,并各附一信。在南京,我公开散发了几十份。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家就热闹了。我的《起诉书》上有地址和电话。常有不速之客,不为别的,远道而来向我表示敬意。电话也很多。用电话表示者,往往不愿讲姓名,我从来不问。 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高兴,见了我就问:“甚么时候开庭?”还有人说:“我们有几千人要去旁听,把它新盖的礼堂挤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刚搬进新盖的大楼,就在南京大学对门,要是去旁听,祗需跨过马路,十分方便。我对他们说:“旁听可以,千万别‘闹事’;你们‘闹事’,对我就是帮倒忙。”他们相对一笑。 原南京大学的学生、吃了两年官司的陈学东看到《起诉书》後来找我,他为民主运动期间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後悔,表示要学习合法斗争。他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意志很坚决。 南京大学党委作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说是全校所有的复印机不准复印郭罗基的状子。大学生们说,不给复印,我们不能用手抄吗?有人告诉我,他至少看到三种手抄本,字迹还很工整。 到美国以後,刘青告诉我,他们在北京约定:谁得到郭罗基的状子,各自复印十份,分发给自己的朋友,依此类推。总共复印了多少,已无法统计。怪不得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打来长途电话,说:“你的《起诉书》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要和你核对一下。”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我的朋友们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有何动静?过了七日,毫无动静。朋友们说,情况不妙。我的估计则相反,我认为法院有麻烦,时间拖得越长对我越有利。 种种内部消息,慢慢地传了出来。 公安部门还是老一套,认为我所散发的《起诉书》的内容是“反革命煽动”,要把我抓起来。中共江苏省委不批。省里的一些厅局长干部是我过去的部下和学生,他们施加了影响:“要说郭罗基是‘反革命’,砍了我的脑袋都不相信!” 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又给南京大学党委打电话下指示来了。不久前,他在长春召开了一个“文科清理会议”,部署“清理”文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点了我的名。“郭罗基又跳出来了”,他要求南京大学党委拿我当典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北京发号施令好说,南京大学党委具体执行不好办。我的《起诉书》产生的影响和大学生的情绪,他们不是一无所知,于是请示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为此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国家教委的意见,认为“公开批判祗能扩大郭罗基的影响”,要求南京大学党委通过个别谈话解决问题。报告送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电复:“同意江苏省委的意见”。 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们开会研究如何进行个别谈话。他们公推党委书记韩星臣出面,韩说:“不行,我说不过他。”又推校长曲钦岳,曲说:“他告的就是我……”最後推定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党委常委董健找我谈话。董健在家学了三天法律,拟了一个谈话提纲,又经党委讨论通过。然後,党委办公室的干部打电话给我:“郭罗基同志,党委通知你下午两点来开会……” 我说:“我已经不是党员,党委有甚么权力通知我去开会?”对方无话可说。 又有一位女士来电话,很和气:“郭先生,我是校长办公室的,校领导请您下午来谈谈。” 我问:“谈甚么呀?” “我还不知道,我去问问。”她去问了又来:“说是谈您的告状问题。” 我说:“告状问题应当到法院去谈。我是原告,校长是被告,有话在法官面前讲。” 她说:“请您等一等。”大概她去转告了我的意思,又拿起电话:“校领导问,您来不来?”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法院通知我,马上就去;到南大谈告状问题不是地方。” 党委以“郭罗基不愿谈”向上交差。董健的朋友告诉我,他很高兴,如释重负。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是英国BBC驻北京记者麦杰斯。我得到您的两份《起诉书》,我们要广播,您同意吗?” 我说:“既然你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起诉书》,也就不必得到我的同意。” 他心领神会,笑出声来:“您回答得很巧妙。” 下午,又有人来电话:“我是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史进德。我的中国朋友给了我两份您的《起诉书》,我想写一篇报道,您是否同意?” 我说:“新闻自由嘛!报道不报道,怎样报道,是你的事情。” 他连连说:“我懂了,我懂了。” 这两个外国人汉语讲得很好。对于我在《起诉书》中提到的事实问得很仔细。 同一天晚上十二点,英国BBC节目主持人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提了五、六个问题,最後一个是:“在目前中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您认为告状有用吗?”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阐述了开展人民护法运动和人民立法运动的主张。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有客来访。一看名片,是新华社驻江苏记者高峰。他说,刚听到BBC的广播。“你告党委,这确实是新闻,所以我也来采访一下。” 我说:“这样的新闻你能公开报道吗?” 他笑呵呵地说:“可以写‘内参’嘛!” 我说:“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上你们新华社的‘内参’,‘参’进中南海,邓小平就点我的名。” 他补充道:“你来南京以後还‘参’过几次。” 我问:“你来采访不会是个人的行动吧?” “当然,领导上打过招呼。” 我想,是“领导上”派他来摸我的底的,因为这时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找我谈话。他问了许多问题,作了详细记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法院不予受理,你怎么办?”他们最怕煽动学生闹事。 我说:“我坚持按法律程序上诉、申诉,但究竟怎么办,还要到时候再看。”我让他们既放心又不放心。 又过了一天,美国之音(VOA)节目主持人东方,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二月二十四日,美国之音播出了一个十分精彩的专题节目。先是放我的谈话录音。接着有两位对起诉事件发表评论,一位是《中国之春》的主笔胡平,一位是未透露姓名的、南京大学毕业後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女学生。这位女学生嬉笑怒骂,言语生动:“我觉得中国领导人真蠢。他们把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关在国内,不让出国,自以为得意。其实是不得安宁。”这一点,大概提醒了中国领导人,後来变得聪明了。他们陆续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出国。但放出国就不让回国,以为从此祸水断流,又过于自作聪明了。这个节目的後半部分更有意思。 东方:“作为被告的南京大学党委和国家教委是甚么态度呢?”电话打到南京大学党委:“你们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党委,知道吗?” “知道。” “你们党委是甚么态度?” “我们……我们没有态度,听法院的。”虽然显得很笨拙,还不算太离谱。 电话打到国家教委党委,说是请政工司答复;又打到政工司:“南京大学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你们国家教委是甚么态度?” “这个……,这事你问外交部,由外交部统一口径。”大学生宿舍里每天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听美国之音,听到这里,不禁哄堂大笑。评语是:官越大越蠢。 东方:“好,我们将打电报给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请他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 後来东方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果真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了,发言人说:“这不是外交问题,我们不能代替国家教委来回答。” BBC和VOA广播以後,我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表示声援,还有从陕西汉中的深山和贵州边远地区写来的。《起诉书》的流传,大概主要是在城市。电磁波比文字传得更快、更广。关心我的朋友们兴奋地说:“这下子你的安全没有问题了!”我说:“中国公民的安全要靠外国的舆论来保障,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三月二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三个人,二男一女,向我送达出庭通知,让我签字,颇为郑重其事。但态度友善,其中一位环顾四周,还找一点题外的话说说:“郭教授,你这是文人之家,很高雅。” 下午两点,我准时到达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已在等候:一位审判长,两位审判员,一位书记员。先是例行公事,核对姓名、年龄、地址等等。审判长开讲,解释一下为甚么审理的时间拖得那么长,说是因为法院搬家。对我的起诉,结论是“不予受理”,理由有三条: 一,南京大学党委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具备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 二,作出“缓聘”和不同意出国的决定是学校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 三,国家教委没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我对这三条当场一一反驳,那些意见已经写进了《上诉书》。 我特别针对第一条反驳:“你们讲的这条理由,我早就想到了。我的《起诉书》是两份,你们却没有注意到。我对国家教委的起诉是行政诉讼案件,当然适用行政诉讼法。我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本来就不是行政诉讼案件。如果一定要问,这是甚么案件?祗能说是‘共产党违法案件’。我找不到适用于‘共产党违法案件’的法律,祗好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法院去解决。你们在不该用行政诉讼法的地方用了行政诉讼法,不是我的起诉不应受理,而是你们自己把适用的法律搞错了。”审判长一下子脸都红了。 我讲完後,他们也没有甚么可讲的了,给我一纸《裁定书》,说:“你上诉吧,上诉吧!”一位审判员提醒我:“注意上诉的日期,十天。”是的,法院违反了程序,裁定超过七日,我无可奈何;如果我的上诉超过了十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布作废。 按规定,庭审记录要本人签字。我将记录作了一些修改。书记员愿意再抄一遍让我签字。等待的时候,就进入非正式会谈。法官们都叹起苦来,待遇低、住房挤。审判员中有一位女士,也就是上午送通知的那位,别人指着她说:“一家三代人,还住着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她本人倒是笑盈盈的,并无怨言。他们大概都是清官。我起身的时候,他们都为我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