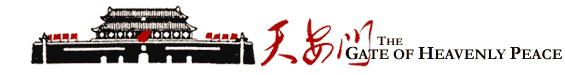 |
||||||
|
诉讼纪实(二)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把党内斗争引向党外?我想抓住收容审查的问题做文章。 六四以後抓人,总是说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甚么法?收容审查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国务院、公安部有过关于收容审查的规定,但它是违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作为行政措施的收容审查,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方面,与逮捕没有甚么区别。这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的逮捕。国务院、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与宪法相抵牾,因而是非法的。在执行中,又不按规定办。本来,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後来主要用来对付政治犯。收容审查的时限是一个月,至多不能超过三个月。而六四以後被收容审查的人已超过五六个三个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是违法的,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拘留逮捕条例》等有关法律。 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抓走以後,一直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收容审查。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递了一封《抗议书》,抗议南京市公安局在收容审查问题上的非法、违法行为。南京市公安局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破坏了大学的教学秩序。我作为研究生的导师也是公安局破坏教学秩序的被侵害者,所以有权提出控告。我还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首先提请南京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我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将手持法律,走向法庭,伸张正义。 这封信写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那时我因病住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在病床上写成的。按常规,南京市人民政府一定置之不理。我的计划是一个月之後以南京市公安局为被告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人民法院肯定不会受理,我再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申诉。另一方面,收容审查的问题并非南京所独有,可以从南京市公安局追到公安部、国务院。不料,我出院後不久,二月十一日朱利全等人被放了出来。不见得是我的《抗议书》起了作用。但下一步法律诉讼的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得另找题目做文章了。 朱利全等人释放时叫做审查结束。另一名物理系学生陈学东,就是那位带领学生堵住长江大桥的高自联常委,被判了两年徒刑;按关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计算,没过多久,也放出来了。既然收容审查的关押可以折抵刑期,怎么能说它是行政措施?可以折抵刑期的长期关押,未经司法机关批准或决定,怎么能说它不是非法、违法? 朱利全出来後告诉我,在他关押期间,重点审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我的关系。真是软硬兼施,用尽心机。第一次提审就要他交待和导师的关系。 朱利全说: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教我学问。 有一次,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找他谈心。朱利全是被关在南京市看守所,由上级的处长出马,可见案情重大。处长说:你的导师有思想,文章写得好,我都看过,就是有些话说得太早了一点。你怎么看?想套他的话。朱利全说:郭老师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北京写的,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看过。郭老师到南京以後就不能发表文章了。 後来,公安人员发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地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了,就看你交待不交待?然後拿出一张单子,上面一行一行地写着几月几日几点到几点。说:你一次又一次到导师家干甚么去了?讲吧! 朱利全看了一眼,他不记得那些日期了,不说话。公安人员提醒他:五月十四日南京市高自联成立,你五月十三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八日南京市大游行,你五月十七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九日鼓楼广场开始绝食,你五月十八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厖都是关键时刻,你干甚么去了?呃? 朱利全又看了一眼,仔细一想,准确无误。他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还问我干甚么!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 高尔泰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发表了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第一稿和他的《异化现象近观》,还有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主编林韦被邓力群指责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而遭撤职。此後,我和高尔泰神交已久,但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南京时他来访才相识,彼此一见如故。时值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对我颇多激励,赠钟馗图一幅。他所画的钟馗与众不同,是一个戴眼镜的现代钟馗,作仰天长叹状,题诗曰:魑魅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後来,他又重画一幅,题诗祗有一句:一个钟馗奈若何。他说,这样更含蓄。此幅钟馗奈何图,我十分喜爱,常悬室中。往还多年,他就想到南京大学来教书。经不少周折,一九八九年居然办成。九月一日,他正从南京的新居出来,上去两个人,是四川省公安厅的,要同他谈谈。一谈不复返,被押回了成都。 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高尔泰作为反革命宣传鼓动嫌疑,被收容审查了。这是因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四川比江苏搞得更凶。北京民主运动高潮期间,各路诸侯中给中央打电报施加压力的有海南的省长梁湘和四川的省委书记杨汝岱。後来,梁湘被找了个岔子撤职查办。杨汝岱一看风头不对,早就转弯子了。为了将功补过,他特别卖力。除了北京,外地开枪的祗有他的治下成都。高尔泰告诉我,六月五日,他亲眼看到武装警察挥舞狼牙棒在成都大街上见人就打。有一个男子怀抱婴儿,狼牙棒打下来,他一闪,正中孩子的头上,一刹那脑浆迸流。这位愤怒的父亲,大喊一声,把死孩子扔向了警察。我久久不能从心头抹去这一幕惨状。事後,杨汝岱抓人也很起劲,还抓到南京来了。高尔泰被关了四个月後释放,得了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在狱中与刑事犯关在一起。那些凶狠的牢头狱霸要教训教训他,反被他打翻在地。他学过武术,当右派的时候又在大西北经受了生死考验,所以有本事把刑事犯镇住。出狱以後,他对我说:当时我就为你担心,你要是被抓进去,受不了厖 我的《抗议书》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後,没有答复;南京大学党委却作出了反应。一月二十八日,党总支书记郭广银通知我:党委决定,因政治审查不合格,取消我当教授的资格。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非法移民向税务局交了税,税务局不得把他的非法移民身分告诉移民局。在中国,官家都是相通的,可以转材料,最後都转到本人所在单位的党委进行处置。对知识分子的处置常常是取消职称或不得提升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重功名,从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变为如今的助教、讲师、教授的职称系列,孜孜以求。《儒林外史》中那些可笑的周进、范进们,换上了二十世纪的新装,还在继续演出传统的悲剧。共产党利用知识分子的功名心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因而提升职称成了政治控制的手段。我对这一套早已看透。一九八九年三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我的博士导师资格。不久,政治风波兴起。有人给我打招呼:你千万不能动,否则博士导师的头衔就丢了。我说:我宁可不要博士导师的头衔,我要做一个像样的人!敁六四以後,博士导师的头衔果然丢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同情惋惜。现在又取消了教授资格,老子不在乎,其奈我何!但是,我也不放弃这一机会进行合法斗争。我给中共江苏省委送上一份《控告书》,控告南京大学党委取消我的教授资格是窃取行政权力、作出错误决定,因而违反了宪法、违反了党章。南京大学党委作出的决定,曾装模作样地在校、系评审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中都有党外人士。我提出质问:我的三点看法属于党内的保留意见,是谁把它向党外人士泄露的?我要求追究,以违犯党纪论处。当然不会有甚么结果,我祗是表现一下有理不饶人。 我对南京大学党委的控告,省委置之不理,反而来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先是党委书记韩星臣在一个叫斗鸡闸(从前是何应钦女儿的公馆)的地方背着我开了几次预备会,统一思想。三月十四、十五日,讨论了两个下午,虽然最後以不予登记的方式取消了我的党籍,但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大大地伸张了正气。 按规定,我必须首先作思想小结、进行自我批评。我全不按规定,还是讲我的三点看法。评议时,这些讲哲学、教理论的同行们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想反驳都抓不住论点。说来说去祗有两条:一,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二,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结论是不能当党员。这两条,我早已直认不讳。正因为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我才提出保留意见;由于提了保留意见而不能当党员,这是侵犯党员权利、破坏党章。现在不作自我批评也是事实,但不是从来。一九五七年以後,共产党的左倾思潮横流,能顶住压力不作自我批评是一大优点,而我还做得不够。第二天下午,支持我的人纷纷发言。六四以後,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分成两派,大体以年龄划线,人们戏称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持官方的态度,又掌握了系的领导权,处处打击青年黑格尔派。也有交叉:按年龄来说我是老年,但政治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有一对夫妇很年轻,政治上却属于老年黑格尔派。会议的高潮是,支持我的青年黑格尔派人物张之沧,与那位老年黑格尔派中的年轻人,拍桌子大吵了一通,火药味很浓。时代确实不同了。一九五七年,刘宾雁受批判时,一位支持他的朋友戚学义当场跳楼自杀,祗能以死表示抗议。一九八二年,我在北京大学受批判时,支持我的朋友也祗是暗中出主意,会上表示沉默。现在是明目张胆了,公开支持我就是甘愿冒犯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L副教授。过去,他因支持我而为领导所不喜欢。他估计,中国的现状还能维持二十年。二十年一过,自己的一生也完了,所以决定转弯子。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你既然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自己提出来不要做党员了。我的那些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他都曾表示赞同,那么他自己为甚么不提出来呢?他也确实想不当党员,祗是考虑到家里有老人孩子才当下去。他对我很了解,我是不会自己提出来不做党员的。第二天,该说的都说了,支部书记要表决。有一位政治上虽保守而心肠很好的人提议:是不是让老郭再考虑几天,下一次会议表决。老郭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党籍丢了很可惜。祗要他表示愿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都可以重新考虑。 L副教授说:这个会开得很痛苦,不要再开了,现在马上就表决。痛苦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双重人格的表演。 又有人说:看郭老师是不是愿意考虑大家的意见,如果愿意,还是再开一次。 他们把拥护官方的态度叫做大家的意见。我说:现在在场的大家的意见也有不同的观点。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考虑,但考虑的结果不能保证大家都满意,再考虑几天恐怕也很难改变几十年的考虑。 L副教授接着说:你看,再考虑几天有甚么用!去年,他对刘广明和我说,我们两人的重新登记,在支部大会上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保证。今年,他却是迫不及待地要求通过给我不予登记的决定。 表决的结果,以九票对七票通过不予登记的决定。祗差一票,如果是八票对八票,就不能通过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甚么都是一致通过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毕竟还是出乎党委的意外,他们本来以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六四以後,我们这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次在支部大会上唱反调的时候,还没有人响应,而现在党内出现了不可小看的反对力量。合法斗争改变了一个单位的小气候,坚持和扩大斗争也一定能改变全国的大气候。 决定通过以後,支部书记让我发言。我说:我再一次表示反对这个决定。我要申述反对的理由,起码讲两个钟头。如果你们不怕耽误吃晚饭,我就讲下去。也可以另外找时间接着开厖其实我是缓兵之计,想把我这个最後的发言组织得有条理一些。当时已是下午六点,支部书记说,那就以後再开吧。事後,他们又赖帐了,说:请示过党委,不同意再开了。我说:那我就写书面意见,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位到会者。 为刘宾雁跳楼自杀的戚学义,死後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为我辩护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没有成为甚么分子,但後来的日子也不好过。L副教授改换了门庭,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被取消教授资格,空出一个名额。他看准机会,改变态度,就补了上去。如果他继续对我表示支持,这个好处不会给他。党的领导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否则,关于我的不予登记的决定就通不过。L副教授又被任命为哲学系副主任,发给特殊津贴,申请多年的换房问题也得到了照顾。林彪把共产党的权术、也是历来统治者的权术概括为一句话:诱以官、禄、德。诱人者是可恶的;但多少知识分子,自愿上钩,失尽尊严,也是很可悲的。维护人格,追求真理,进行合法斗争,不仅要耐得寂寞,而且同样会忍受牺牲;这种渐渐消磨的牺牲更难熬,更需要韧性的战斗精神。 我的目标是走上法庭,但还没有找到打官司的题目。清洗出党不是法律问题,但我深知共产党的脾气,对于被清洗出党的异教徒,必将进一步实行政治歧视和迫害。我耐心地等待着共产党为我创造诉讼的条件。 果然,一九九一年暑假以後,九月十二日下午,哲学系主任林德宏和新任党总支书记钱惠琴找我谈话。林说:上午系里开了会,根据上面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决定,你的课不上了,由别的同志来上。 我多年来讲授研究生必修的专题课。六四以後,我发表不同政见祗限于党内,上课还是按教学大纲讲,所以没有理由不让我讲课。现在不让我讲课,肯定是有上面的精神来了。 我问:搼上面的精神是甚么?根据目前的形势为甚么就不许我上课?请你们讲出理由来! 林说:上面的精神你应该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请你讲一讲。 谈话冷场,谁都不讲话。 系主任林德宏是看上面的脸色办事的人。一九八二年我初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时,这里人与人关系融洽,系主任夏基松主持公道,因此气氛极好。文化大革命以後,这样的单位可以说全中国少有。当时我很庆幸,心想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蒋南翔选错了地方。系主任换上林德宏以後,搞得人心离散,四分五裂。他有一句口头禅:多做工作有甚么好处!他当系主任就是为了捞好处。利益不均,必然引起矛盾。下面没有多少人拥护,则唯上是从。所以,越是贪官越听话;越是腐败官僚机构的权越大。林德宏对上面的精神当然很清楚,不知为甚么他就是不说。我就是要逼出上面的精神来。 我说:既然你说不出上面的精神,我无法执行,到时候我还是去上课。说完就走。这次谈话不到一刻钟。隔了一天,林德宏、钱惠琴又找我谈话,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们说,是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一起作的决定,因为我有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合格,所以不能上课、不能带研究生。钱惠琴还说:我们是婉转地传达,他们说得很不客气。 我说:第一,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我保留以後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二,取消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是撕毁协议的行为,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钱惠琴很紧张:你要采取甚么行动?我劝你不要采取行动。在她看来,采取行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我说:我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然後她就对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陈词滥调说了一大堆,最後一再强调:希望你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我说:马列主义,我比你学得多。你看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你说说。 她说不出来,脸通红。事後,她对人讲起这一点,大为不快。 钱惠琴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基层政工干部。她上过大学,因为教书教不好、研究做不了,转为政工。大学里的政工干部大多类此,是教学第一线淘汰下来的人物。某人,搞教学讲师都当不了,搞政工则可以当个科长;过几年又可以提升为副处长、处长。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处长相当于教授;不仅相当,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工教授、德育教授、管理教授等等。智商很低而又曲线追求名利的人,都集中到政工干部队伍中去了。其实,这批人是给共产党帮倒忙。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说过,北大办得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当校长,蔡元培只身上任,根本没有甚么政工干部。政工干部们听了当然很不高兴,说我否定政工干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好像也有所感觉,他曾说:大学里祗要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但後来要反自由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政工干部。在共产党看来,维护稳定比办好教育更重要。而依靠一帮愚蠢的政工干部来维护稳定,共产党的形象祗能越来越糟,饮鸩止渴而已。政工干部们常常板起马列主义的面孔教训人,他们自己又不懂甚么马列主义。我的专业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这一套对我失灵了。 听说上面的精神来自国家教委,但没有拿到证据。正巧,证据来了。 周培源先生来南京。我们是忘年交。我和妻子刘渝宜去拜访。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物理系教授冯端也来了。冯端是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不改常态。曲钦岳却点头哈腰、形状畏葸,因为他有求于周老。我看到了两个曲钦岳:在小人物面前是一个高傲的曲钦岳,在大人物面前是一个卑下的曲钦岳。我想起了《官场现形记》中的描写,脏官的官服都需要两套:在百姓面前得穿前襟长、後襟短的官服,因为老是挺胸;在上司面前得穿前襟短、後襟长的官服,因为老是弯腰。曲钦岳如果穿长袍,现在就需要前襟短、後襟长了。 我妻刘渝宜问曲钦岳:不让老郭讲课是你决定的吗?为甚么在党内发表了不同看法就不能讲课? 曲钦岳说: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我不清楚。政治上的问题由党委拿意见,我不好插嘴。行政上的事嘛,我不能说不清楚,那是执行国家教委的规定。 以不是党员而当大学校长,为数极少,因为像曲钦岳那样的人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中国的民主人士往往比共产党员听话,共产党内还有持不同政见者,选听话的民主人士当政更便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民主人士本人来说,也乐意如此,有好处是自己的,有麻烦就推给党委。 刘渝宜又问:国家教委的规定有文件吗? 曲钦岳说:文件没有,是口头的。教委负责人在各种会上多次讲过,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 这样,我就可以把哲学系、南京大学和国家教委连成一条线。 我收到一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英国的国际传记研究中心和美国的传记研究所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几种名人录。这两个机构联合向我发出邀请,参加将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文化和交流大会。我向系主任递交了一个要求办理出国手续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的费用自理。我算了一下,总共需五千美元。我负担不起,即使批准出国我也去不了。但我断定上面是不会批准的,可以使我又一次拿到侵犯公民权利的证据。过了一个多月,系主任答复:请示过党委,党委书记韩星臣说:像他那样的表现,根本不能出国。挃好极了,比我预计的还要好,我正需要这样的材料。公民出国由共产党的党委来审批,而且可以根据表现限制出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已习以为常,我的一些朋友,即使思想很解放的朋友,也表示困惑:这怎么是违法行为?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慢慢腾腾地说:也有道理厖。不过,还是提醒我要谨慎,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教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触犯党的领导是要当右派的。这就更促使我运用法律武器来对付党的领导。 中国的现实是党政不分。但我的起诉不能党政不分,虽然违法的事实是相关的。我分别以国家教委、南京大学党委为被告,进行起诉。同我直接打交道的是南京大学和哲学系,他们不是行政机关,根子追到国家教委,就构成行政诉讼。我起诉南京大学党委,还想引出一般性的命题:共产党违法。苏联解体以後,苏联共产党的存在是否合乎宪法引起诉讼。这一点对我有启发。但此时提出问题,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何不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起诉共产党? 我知道我的官司在法庭上是打不赢的,但在道义上一定能打赢。我的诉状主要不是给法官看的,而是给人民看的。这就决定了状子的写法。起诉书有一定的格式,逐栏填写则索然无味。我不去管它,自成一体。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抗议书》是手写的,复印了几份,作为抄送件给有关单位。其中一份给了南京大学学生会,他们又去复印了许多。这事提醒了我。我几次要党委把我的发言打印出来,他们不干。我决心自己买一台电脑,写作诉状,便于打印、复印,以广流传。 当时我手头拮据。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後,祗发基本工资;听起来还是基本的,其实祗是全部实际工资的一小部分。後来发职务补贴,我的职务补贴在助教之下。我问校长,我算甚么职务?没有答复。为了表示抗议,我拒绝领取工资。这样,我就没有收入,靠朋友接济。恰好有一笔意外之财。台湾时报文化公司将我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收入丛书,给了六百美元稿费,换得三千三百元人民币。我走进一家电脑公司,老板说,不谈生意,先谈友谊。电脑是现代化的,经营电脑的人脑也比较现代化。当我得知一台IBM286的电脑售价是三千九百元,面有难色:我祗有三千三。对方却说:好!就三千三。你郭先生要用电脑,我们送你一台都是应该的。那种电脑的进货价是三千四,临走还送我一个多用插座和五张软盘。我在中国办事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是明码的自由化分子,办事的时候对方知道我而我不知道对方。如果遇到反自由化人士,往往横生枝节,多方刁难,自以为很有把握的事也办不成。如果遇到心心相印的人物,则排难解纷,锦上添花,别人办不到的事我能办到。後一种情况越来越多,使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 |
中文主页 | 关于影片 | 音像图库
| 民主墙 | 六四史料
| 网站导览 | English
©
Long Bow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